走近苏东坡
——读《望美人兮天一方》
李廷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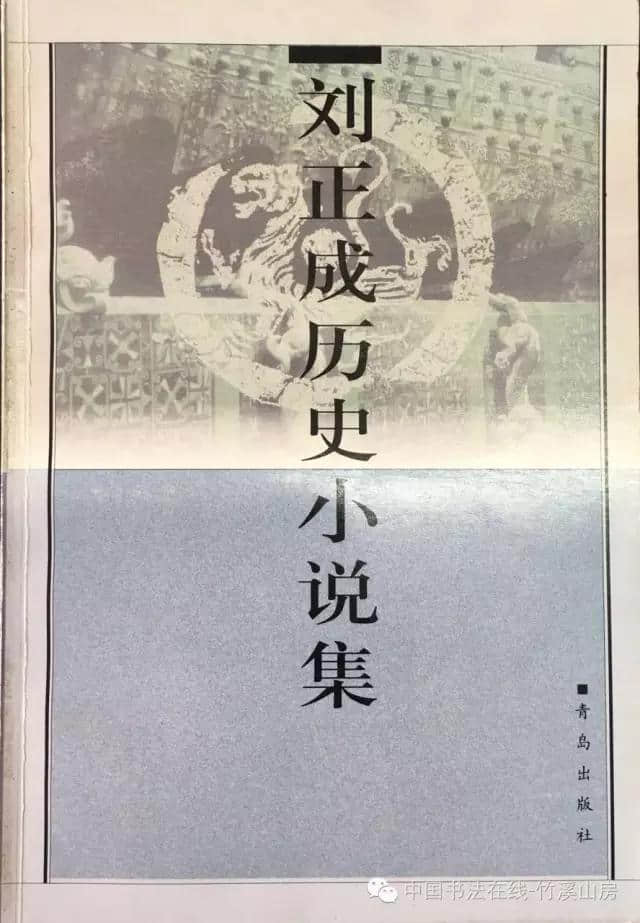
翰章情采从头读,最羡人间有大苏。
心了黍黎三两事,神游天海万千途。
禁碑伐党存昔谬,文气漂萧愧陋儒。
且看风清月白里,江船醉卧倩人扶。
谪仙人李白离我们比较遥远,而“坡仙”则要接近一些。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传》,写到后来,也渐渐漫漶而寡味;但他对苏东坡的一往情深,他的跳出中国文化圈子、立于人类文化视野对苏东坡的那些评价、则是极为精采,又极为肯綮的。林语堂以为:在苏东坡身上,集中了中国文人的特点、优点。苏东坡的爱妾朝云曾说过:“相公一肚皮不合时宜”,被苏东坡引为知己。和这句堪为妙对的是苏东坡的另一特性:“满眼间皆是好人”。苏东坡的哲学,浓缩起来就是一句话:“既看破又不看破”。以苏子之智,早就参透了人生真谛,“纵一苇之所如,观万倾之茫然”,这时的苏轼是庄子;徐州抗洪,杭州筑堤,参吕惠卿,平反后又反过来替王安石说话,得罪自己“风雨同舟的战友”,这时的苏轼,竟然又有些像魏征,是真正的“文死谏”,是大儒、真儒。
刘正成写了《半山唱和》,在那天开画屏之中,主人公是王安石,却不能不让苏轼得半壁风光;意犹未尽,他又写了《望美人兮天一方》。在此篇中,他则通过徐君猷的眼光,渐渐走近苏东坡。他写苏东坡的睡相:“他无意之间得见的这病汉般灰颓落寞的苏轼,他觉得正在解开一个迷:人睡了,矫饰他外表的那精气魂灵便暂时归于消亡,而暴露出的,不就是他的真面目!”
《赤壁赋》所寄寓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刘正成神游其间,他借徐君猷之思:“一个犯了杀头之罪的囚徒,他的痛苦好像不是自己苟延残喘的现状,竟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样。这不是一种奢望么?他的心悸动了一下,似乎发现了一个两三年来毫无所察的隐秘:一个人超群出众之处,也许就是这种‘奢望’带来的吧?不过,这种‘奢望’所伴随而来的痛苦,不是更为沉重得多吗?”这里,刘正成的笔触,很自然的又进入了亘古常萦人类的“思绪”。
徐君猷身为州群长,是羁管“钦犯”苏轼的顶头上司。苏轼的不世才华和人格风范,使他倾倒折服;他也冒着风险,替苏轼多方回护,同时,也得到了苏轼的理解和敬重。然而,苏轼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稀罕,当苏轼在赤壁之下,发思古幽情、抒人生宏论时,徐君猷便不能不心怀畏惧,他不能不婉转地劝告:“多想往事,徒生烦恼,有害身体……”。然而,苏轼竟迳出此言:“不平则鸣!人不能谈国事,竟不能作诗么?人之奢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慨怨怒,有不顾其死者,什么样的严刑峻法,又其奈何哉!何况,像我苏轼这样已经死过的人了,又何惧乎?”
苏轼是曾经怕过死的:“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浇汤火命如鸡”。然而,也正是对生命消逝的惊骇和人生意义的掂量中,他似乎得到了解脱。刘正成代苏子立言曰:“人,既然已死过一回了,那么,对生死大约就没有那样介意了。人是无来由而生的,也会无来由而死,正所谓平生生死梦,三者无优劣耳!”
苏轼诗文传世,以《念奴娇•大江东去》为压卷。此时之苏轼,在徐君猷眼中,从功名盖世的曹孟德、周公谨,萦忽而成独立世外的庄周。苏子究竟谁何?徐君猷一时湖涂了。“望美人兮天一方”,谁是苏子心中真正的“美人”呢?
“君不知,吾非公谨,吾非庄周,吾乃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居士苏轼也”。苏东坡,这个天人合一的精灵,这个恒古不泯的“美人”。刘正成写《半山唱和》和《望美人兮天一方》里的苏东坡,他写不够,又写了《苏东坡书法评传》,这片钟情,也真可使人神往。
望美人兮天一方
刘正成
黄州知州徐君猷在城南办完公事,看看时间还早,设法把随行执事人等打发回去,只带一个马僮,准备去看苏轼。
三年前,也就是大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侥幸免死,被罚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即是流放此地给看管起来。苏轼是因作诗和言论,差点被朝廷问斩的,朝廷格外开恩,全了他一条性命,倘若重犯前科,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因之,在大多数同僚眼中,徐君猷是秉承上司旨意,亲自监察犯官苏轼言行,以便按时向朝廷呈报的。
徐君猷并未急着出城,待随行众人远去以后,却叫马僮去市场买了不少蔬果鱼肉,随后,才出城往苏轼的住所临皋亭而去。
不一会儿,便来到几间孤零的茅亭草舍前。马僮上前叩门,蜷卧门边的一条黄犬早腾起来汪汪吠叫开了。柴扉开处,是长得与父亲苏轼颇为相象的苏迈。苏迈见了徐君猷,连忙躬身请安,回禀家父正在江边散步,说着便要去找人。徐君献朝江边望了一眼,拦住苏迈。打算自己去找。临走时,苏迈面色有些忧郁地走近他,小声告 诉说:这几天饭后,苏轼午眠也不顾,便一人去江边,直到薄暮方回;回来后总要长吁短叹,情绪很是不佳。徐君猷听了,觉得有些意外。
这临皋亭住南,不到百步,便是大江。徐君猷独自来到江边,放眼望去,但见江岸空阔,并无一个人影。他停住脚步,脱下青丝头巾,撩起前襟一角擦擦额头汗珠,再倒握折扇从后腰伸进背心,撑起汗湿的纱袍,一任凉风吹拂。转瞬间,徐君猷便觉得暑气大消了。
东边江岸乱石挡道,他便抬腿往西。走了好一段路,来到一个颓圮的营垒。这里遗础残砖,一片狼藉。他小心翼翼穿过这营垒,又费力攀上一个陡坡,便能远远看见那像一只巨斗插入江中、石色如丹的赤壁矶了。这长江西来,流到赤壁矶脚下,便折向南去。因之,这转弯的浪涛雪崩也似,争先恐后而至,狂怒地冲击堤岸乱石,发出轰轰吼声,随江风掠来,震耳惊心,徐君猷想坐下歇息一会,因为他觉得从这里看赤壁,很美。他看见不远处正有一株孤树,当他渐渐走近时,才发现树荫下一方大青石上,早已卧着一人。当然,要不是江风拂起那件麻褐色宽袍的长带上下翻飞,他定会恍然误认为一个蜷曲的盘石哩。
“子瞻!”徐君猷在心中立刻想到,口中便也叫了一声。那人却未答应。他几步走到跟前,果然是闭目而卧的苏轼。不过,这眼前的苏轼,却令他倏生惊诧。
月余未见,苏轼那张金钟也似宽额广颐的长方脸膛,晒得墨一样黑。两颊被刀削过一般,变尖了;上面原本潇潇洒洒的络腮胡子,眼下竟像一蓬枯草。那一顶颇有些凛然不可冒犯的短檐高筒青纱峨冠,却攥在手中,这手,也许攥得过紧,指节暴突,捂在心口上,好似心口有难忍的疼痛。木屐想必睡后脱落,一仰一仆散在青石下,露出的脚底白得没有血色。徐君猷觉得这俨然一个气息奄奄的病汉,哪还像那个倜傥调侃、先声夺人的苏子瞻?
徐君猷对苏轼的推崇,是至为真切的。在他眼中,当今天下名士,苏子瞻第一。其诗词书画,道德文章,无一不得尽风流。苏轼贬居黄州后,得以亲自过从其间,苏轼不仅令他倾倒,更使他无形之中改变了许多对人生世事的看法。
苏轼自来黄州后,凭着一家人的手足,在这里拾瓦砾,种黄桑,刈草盖房,有时穷到揭不开锅,用他自己的诗来说,“形容虽似丧家犬”啊!处如此至贫至困之境,毫不改其乐天旷达的本性。种田谋生,他竟不觉厌烦,倒有许多兴致似的。临皋亭、东坡、雪堂,这些个寒枪之极的处所,未得亲见之人,真会误作桃源仙境呢!元丰二年,苏轼在湖州任上被钦差拘捕,生离死别之际,王夫人哭得死去活来,他倒讲起笑话来。他讲,真宗时,有个善诗的隐士杨朴被召见,皇帝问他能诗否,他说不能;又问他有人作诗送行否,他说只有老妻作了一绝:“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听后大笑,便把杨朴放还了。讲到这里,苏轼对夫人笑道:“轼也因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卿难道不能学杨处士之妻,作一诗为我送行吗?”一句话,把王夫人逗得破涕为笑了。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往返谈笑之间,可以使你喜、使你怒、使你哀、使你乐;喜怒哀乐之中,竟令你不知此身谁身,今夕何夕也。早觉仕途暗淡、生活乏昧的徐君猷,便受到了这种感染。因之,他竟不顾朝廷耳目,想方设法接近苏轼,或诗酒、或冶游,变得达观超脱起来。有人曾当面讽刺他想做个苏轼第二,他毫不生气,反自叹道:“能追随子瞻左右,乃人生难得之赏心乐事也!”
不过也有一点遗憾,则是他觉得与苏轼在内心中多少有些隔膜。这隔膜,并非苏轼对他有什么冷遇(苏轼对他素来热情和感戴,这倒不仅因为他时常对他解囊相助,多方关照之故),而在于他对苏轼内心一隅的莫测。结友而不知心,难免不起烦恼。他总不明白,苏轼对自己这种不见尽头的冤狱羁押、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怎么能如此长久忍耐下去。从不对人道露排遣。难道他竟不懂得,把心中的忧闷,怨愤和痛苦掩饰起来,反会生出十倍的忧闷、怨愤和痛苦?素不愿说三道四的徐君献,终于也忍不住当面影射过几回,均被苏轼一笑置之,回避得很干净。是他对我这个顶头上司有所顾忌,还是不愿让我多担一点干系?他不得要领。而此刻,他无意之间得见的这病汉般灰颓落寞的苏轼,他觉得正在解开一个谜:人睡了,矫饰他外表的那精气魂灵便暂时归于消亡,而暴露出的,不就是他的真面目!然而,能够矫饰他外表的那种精气魂灵又是什么东西呢?他重归于茫然,他想一把推醒他,追问个究竟,忽然心口又起了一阵悸动,蓦地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寻到这里来,就像不该闯入别人内室,窥人隐私一般。
“哟,太守大人驾到,犯官苏轼如此失敬,死罪死罪!”
正在犹豫难堪的徐君猷,被叫声惊了一下。苏轼已醒来,从大青石上翻身落地,正向他拱手作揖;他那双细长眼睛,忽闪着诡秘的笑。要在平日,徐君猷早给这谐谑的动作逗笑了,可今天,他竟笑不起来。
“子瞻,江风好大,怎么到这里睡眠?”
“好做梦。”苏轼用脚去勾那只葡着的木屐。
“这里?”
“是的。你刚刚就搅了我一个好梦!”
“我……”
“你猜我梦见了谁?”又是一个故作诡秘的笑。
“猜不出。”
“非猜不可!”苏轼圆瞪双目,就像一个顽童在发怒。
“自然是梦见周公了。”徐君猷敷衍了一句。
“周公倒是周公,可不是周公旦。”
“又是哪家周公?”
“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苏轼那样认真地说着,转过睑去,遥望西边在夕阳下正放着红光的赤壁矶,若有所思。“君猷,我问你,这赤壁矶果真是三国周郎赤壁?”
“大家都说是吧。”徐君猷随意应了一声,心中却在猜度苏轼这个白日之梦的含意。苏轼这样津津乐道自己这个梦,倒令他想起了庄周化蝶的那个梦。他叹了一口气,道:“周公瑾十六岁便当上了东吴大都督,彼一时也;嘿嘿!你我呢,看这快白了的胡子吧,此一时也!”
“啊……”
背着而立的苏轼,长长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沉默了。一会儿,苏轼把手中那顶短檐高筒帽戴上头。帽子已揉得很皱,蔫趴趴的,总戴不正。徐君猷瞥见那双戴帽子的手在轻轻颤抖。
“子瞻。”
徐君猷叫了一声,苏轼竟没听见似的,一动也未动。徐君猷恍然察觉了刚才那句话的冒失。不知怎么,他忽然感到苏轼在背着他垂泪,因为他那两只肩头也像在颤抖。徐君猷觉得有些害怕。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徐君猷抬头看看天色,说道。
“君猷!”
徐君猷走出好几步之后,猛然听见苏轼大叫了他一声。他有点惊慌地回过头来,看见苏轼那张黑脸变得好长、好冷,一只向他招的手凝固在空中,竟像一个遇难的人在呼救。
“你……别走。”苏轼这句话像给喉咙粘住似的,含糊而小声。
徐君猷赶忙走向苏轼而前,好似恐怕个病人被摔倒。
“多少天了,没有收到亲友们一封信,没有一个朋友来访,大家把我忘了……”
苏轼这一提,徐君猷才恍然记起,自己已有一个多月未来看望朋友了。不过,也使他意外地发现。一个人可能在朋友心中的分量。如果真是这样,他宁愿撕开那隔膜,把无论多么沉重的痛苦分担到自己心上来。
“我真后悔,没有早走到这段江边来,从这里看赤壁,竟是这样美!”
“真的,你也觉得这里美,君猷!”苏轼孩子似的高兴起来。
“刚才在市上,我觅得了一条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妒的大鱼,今晚夜游赤壁如何?”
“好啊!”苏轼乐得蹬了一下脚。“我正酿有一坛蜜酒,曲子不太好,苦了,不过比官酿好得多!”
待苏迈和马僮把酒食搬上船后,船便离了临皋亭江岸,逆流而上,向赤壁划去。一会,便见一轮桔红色满月,从背后跃上东山之巅,播下一江鱼鳞似的光斑。苏轼呼地吹灭了灯笼。
这长江,出了三峡之后,江面便宽阔起来;流至黄州一带,更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尤其这夏末秋初,潦水暴发,驾一叶扁舟,航行大江之上,真宛若一片苇叶,漂浮沧海之间,烟波万顷,淼淼茫茫,而不知其所止。
月光中,徐君猷见苏轼喜形于色,连连催促把船划得快一点。到了晚上,这江水似没有白日里那样奔涌,显得平缓,可逆水行舟,终不能很快,苏轼一把从儿子手中夺过浆来,挽袖便划。那桨撞在船舷上,发出“啌!啌!”的响声,在寂静的江面上振荡;溅起的水花,飞到徐君猷脸上,使他惊了一跳。
“啌啌”的响声忽然停了,苏轼伸长脖子,侧耳在谛听什么。一阵江风拂来,有人**。一会儿,这箫声便越来越大了。箫声很有些悲凉的意兴,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艘黑糊糊的大船在江心逐流而去。而那远去的箫声,却像刚刚生起的白露在江面缭绕,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使人平空起来许多愁绪。
“乓”一声,苏轼把桨扔了。
桂掉兮兰桨,
击空明兮泝流光。
渺渺兮余怀,
望美人兮天一方!
一个雄浑,然而腔调生硬的歌声猝然迸发,连江水也为之颤动起来;刚刚消失的那悲凉的箫声,俨然它的序曲一般。苏轼把脖子伸得很长,用力地唱,一边用手扣着船舷奏节拍。一段高亢、却沙哑的拖音完结后,江面顿时静极了:空气、水、星月,似乎都已凝结;一个失去躯壳的魂灵,在头顶惊恐地盘旋;远处忽断忽续传来几声凄厉的啜泣。徐君猷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在想,投生世上,多像在这沧海之中漂泊,当有狂风巨浪袭来,掀翻航船,堕落水中之时,人还有什么希求呢!除了求生,将别无奢望。然而,有的人则不同,在这样的境况下,他想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苏轼所唱的“美人”是谁呢?是他自己,还是想成为自己的他?一个犯了杀头之罪的囚徒,他的痛苦好像不是自己苟延残喘的现状,竟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样。这不是一种奢望么?他的心悸动了一下,似乎发现了一个两三年来毫无所察的隐秘:一个人超群出众之处,也许就是这种“奢望”带来的吧?不过,这种“奢望”所伴随而来的痛苦,不是更为深重得多吗?
“赤壁到了,这船还划不划?”
苏迈的喊声打断了徐君猷的思索,他抬起头来,迎面看见赤壁矶像头蹲伏的怪兽,头顶上闪着幽幽的光,兀然立在不远处的江面上,一片濛濛的白雾,在它的腰间和足下游荡。
“划到回水处。就任它漂。”
坐在船首的苏轼命令道。他也正在遥望那黑森森的赤壁矶。赤壁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小船被赤壁的阴影笼罩了。
“喂!”
“喂!喂!喂……”
苏轼像小孩一样,用手掌圈着嘴大叫了一声,赤壁便应答他一串回声。刚才歌唱时的忧愁似已消失了,赤壁像一个神秘的怪物,把他的神智给攫住了。
“君猷,周公瑾果然在这里火烧曹孟德的?”苏轼并未回头地问。
“不然,那石壁怎么会是红的。”徐君猷听见苏轼又在重复他下午在江边时的问题,觉得有些好笑,便也凑趣地道。
“君猷,你也会说笑!”
苏轼嗔道,但心里并非不高兴。他霍地站起身来,像检阅三军一般,朝宽阔、苍茫的江面环顾一周,朗声道: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是呵,不过如子瞻兄在大青石上的一场午梦耳!”徐君猷被苏轼这一段慷慨悲凉的陈词所触动,真诚地附和道。
“梦?”苏轼被惹恼一般,竟含着怒意地反问道。但这怒意显然不是向着徐君猷,而是向着在幽冥中与他窃语交谈的那个人。“人生能在如此江山胜景较量一翻身手,便灰飞烟灭,又何憾也!……然而,我苏轼无非作了几首歪诗,发了一点牢骚,便差点掉了脑袋,被掷到这里,做一团行尸走肉,不亦悲乎!”
“父亲,过去的事情,又提它做啥!”苏迈插嘴道,并悄悄嗓了徐君猷一眼。
“哧!”苏轼回头对苏迈瞪了一眼。“你担心个啥?你君猷伯伯是什么人?要不,我就是当一个哑巴,恐怕也不能平平静静过这两三年!君猷,你说是吧?”
“嗯,是……不过,贤侄的话也有一些道理。”苏轼的信任,徐君猷是很感激的,但他想起上司每每察问苏轼在黄州的言行,自己虽多方遮饰,但究竟难以掩众人之口,谁知道灾祸啥时降临?自己担着干系不说,这于苏轼总归很不利。他知道这个话不好明对苏轼说:说了,激怒他,便愈发不可收拾。想了想,便改口道:“多想往事,徒生烦恼,有害身体……”
“嗐!”苏轼带着一种惋惜打断徐君猷的话。“君猷难道未闻韩文公云:不平则鸣!人不能谈国事,竟不能做诗么?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慨怨怒,有不顾其死者,什么样的严刑峻法,又其奈何哉?何况,像我苏轼这样已经死过的人了,又何惧乎?”
“哈,死过?”徐君猷觉得苏轼的话有些怪异。
“不信?你知道我有两首绝命诗吗?”
“伯父,事情是这样的,”苏迈忙解释道——他显然是想把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家父被关在御史狱里,与我相约:平时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有一回,我有事,便拜托一个朋友送饭,却忘记交代这个规矩;朋友正好送去一条角,便使父亲虚惊了一场。”
“这诗,倒实实在在是我在鬼门关前留下的真情实感!给子由的,念一首给你听听。”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是一种凄枪的呜咽了。江面袭来一股寒风,徐君猷觉得脊梁骨阵阵发冷,浑身毛发也竖立起来了。末了,他看见苏轼木然呆坐了一会儿,然后端过刚刚酾满的那瓢酒,仰头便朝嘴里咕噜灌去。“父亲!”苏迈惊醒似的,从苏轼手里夺下那葫芦瓢时,酒已快喝光了。
“人,既然已经死过一回了,那么,对生死大约就没有那样介意了。人是无来由而生的,也会无来由而死,正所谓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耳!”
言罢,苏轼的身子在左右晃荡。苏轼好酒而量小,自谓平生三不如人:着棋、饮酒、唱曲。以至“只要看到酒,太守就醉也。”今天晚上,苏轼的酒喝得确实不少,但毕竟是家酿蜜酒,何以醉得这样快?徐君猷凑近去看,见苏轼已闭上两眼,月光下,那张脸、那些枯草似的胡须,一齐闪耀着惨淡的光。
“哟!这船漂到哪里了?”徐君猷的家人在问。
“不好!已过武昌①了,快朝岸边划!”苏迈急忙去搬那船舵。
① 此武昌,即今鄂城,在黄州下游。
大家手忙脚乱,终于把船弄到江边时,苏轼已醉卧在船舱的角落里了,口里一边呼呼喷着酒气,一边时断时续说着梦话。
赤壁夜游之后,大约是因了苏轼那自酿的蜜酒,徐君猷回到家便闹腹泻,旬日之间,方才复元。后来。他几次想抽空去看一看朋友,因他心里对苏轼的身体、心境这两方面,均有些放心不下;但是,衙里、家中总有诸事缠身,不能成行。转眼到了八月底的一天,也不知从哪里,忽然传来“苏轼病亡”的噩耗。徐君猷当即惊恐失色,继而便举袂大恸,悲不自胜。当时,要不是有人劝阻,先派了人去证实清楚的话,他早已具金帛亲往临皋亭吊丧去了。事情当然很快澄清,原来,也是那次赤壁夜游之后,苏轼便害了一场赤眼病,一个多月不能出门,连偶尔一至的来客也不能见,旁人便猜测他患了什么不治之症,乃至生出此种谣言来。徐君猷自知受了一场虚惊,但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准备亲自去看看。谁知,一耽搁又是几天。九月初的一天,又传来一个关于苏轼的惊人消息:“苏轼夜作一词,挂冠服于江边,乘小舟长啸而去。”徐君猷手中还真得到了这首词的抄稿。其词调寄《临江仙》,曰: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起初,徐君猷对此消息不免有些怀疑,这自然是因为几天前那个讹传,弄得他差点闹个大笑话。待他略作思索之后,心中一动,迅即去书桌上寻到苏轼那篇《赤壁赋》——这是几天前,他派去临皋亭探讯消息的家人捎回的。苏轼在病中作了此文,记述七月夜游赤壁之事。但他在附给徐君猷的信中,一再叮嘱不能示以他人。当时,徐君猷因听说苏轼未死,不禁大喜过望,把那篇《赤壁赋》只粗粗浏览了一遍,便顺手夹在一叠书里去了。此时,他把它找出来,与这首《临江仙》对照着细细读过之后,“啊”地拍案惊叹一声,便深信此一消息决非出于虚无。随之,心中亦大人惊骇了:这倒不仅因为他是州长官,州失罪人,罪责难逃;且料定苏轼贸然出逃,凶多吉少。偏偏那个颇为自得的推官,也得知苏轼出逃的消息。跑来请示徐君猷,是不是立刻派人去缉拿。徐君猷自然没有批准这个刑狱官立刻 派人缉拿之议。他暗自寻思,我徐君猷虽不能与苏子瞻同道,至少也得顺水推舟,稍尽绵薄;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怎能做得。他以“弄清真假再行定夺”为由,把推官打发之后,便吩咐爱妾胜之即刻把家伎们盛饰起来,赴城南临皋亭拜访苏轼。他想,用这样的办法,一则可以暂时遮掩一下苏轼出逃的风闻,拖延点时日,让苏轼稍稍得以从容行事;再则;万一这又是一个讹传,见到苏轼,大家也不失体面。因之,一切停当之后,徐君猷便带着一队伎乐,或骑马、或乘轿,颇示悠闲往城南而去。
读一首诗、一阕词、一篇文,倘能掩卷之后,它竟萦绕心怀,久久不去,或让你陶然欣然,一咏三叹;或让你若有所悟,茅塞顿开:恍然有象外之形、弦外之音、境外之意从中脱颖而出,便不失为一首好诗。一阕好词、一篇好文章吧?而此刻,徐君猷骑在马上,便是得到了此种心境。他只觉眼前忽地一亮,抬手猛一掌击在自己腿上,震得胯下的马也惊了一跳,昂首嘶鸣起来。
苏轼曾经给他讲过,年轻时读罢《庄子》一书后喟然慨叹道:“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而目下这篇《赤壁赋》岂不胜过一部《南华真经》!“苏子瞻者,庄周之再生也!”徐君猷差一点把心里想到的这一句话喊出口来。
这时,苏轼夜游赤壁扣舷而唱的那首歌,幽幽响在耳畔:“……望美人兮天一方!”这“美人”,徐君猷曾猜过是雄姿英发的周公瑾,而今,他已料定是遗世独立的庄周。虽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矣!“嗤!”徐君猷从鼻孔里喷出一声笑来:那《赤壁赋》中所谓主客对话,各执一端,岂不就是苏子瞻的自我解嘲?如今,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岂不就是去遂其“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宿愿么?他又记起了苏轼在赤壁江边青石上的那个梦。他想,他心中要否定、要排斥的,正是像周公瑾、曹孟德那样建功立业的梦想——虽然他心中难免一种痛苦。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岂不智哉!越想,徐君猷越觉得他已真正摸到了苏轼的心,对苏轼的隐遁逃世,已绝不置疑了。虽说到了临皋亭,得知这终于又是一个讹传后,他仍旧毫不动摇自己的想法和推测。他认为,苏轼之出走,无非时间早迟而已。
那天,徐君猷一行赶到临皋亭时,苏轼父子均不在家。王氏夫人和其爱妾朝云向他道了事情原委:几日前,病愈的苏轼去东坡雪堂夜饮,大醉后独自一人返回临皋亭时,已是深夜,家僮熟睡,门敲不开。他便高声唱了一首新填的《临江仙》后,寻到江边,雇了一只小船,连夜逐流往沙湖麻桥庞安常那里去了。接着,又同庞安常去蕲水游清泉寺,直到昨晚方才回到东坡,住在雪堂,至今未返临皋亭来,两个妇人显然把它当作一段笑话讲述后,宽慰和轻松地笑着。“这就好,这就好!”徐君猷也颇示欣慰地附和道。他当然不会对苏轼的家眷道出自己潜藏心中的看法来,他只想立刻见到苏轼,他要苏轼亲自印证自己的推测。因之,他吩咐随行人等,立即兼程赶到东坡去。
夕阳染红的东坡上,早该成熟而尚未成熟、稀疏纤弱的稻秆,在秋风中摇曳不停。徐君猷下马后径直奔向雪堂,还隔卧榻好远,便已听到苏轼的鼾声。两人相见后,均无言地大笑起来;大笑之后,便在雪堂摆开了酒席。胜之率领的一群家伎,经过一番休息之后,已恢复了精神,一齐来到堂上献技、侑酒。一时间,座落在一片荒野中的雪堂,乐声大作,歌舞翩跹,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席间,苏轼好像有意回避似的,许久不谈正事。徐君猷极想听苏轼亲口讲一讲刚刚过去了的一番变故,了解他下一步的打算,同时,也很急于对他推心置腹,以释朋友之怀。但是,好几次,话到嘴边又缩了回来。在苏轼今天对歌舞酒食所表现出的特别兴趣中,他觉得眼前之苏子瞻,已非刚才心中之苏子瞻,亦非七月间夜游赤壁之苏子瞻了。这不由不令徐君猷生出一种惘然若失之感。
“啪!啪!啪!”苏轼大笑着,不停地鼓掌为胜之喝采。胜之正在跳她最为拿手的《柘枝》。另一个舞伴已经悄悄退到一旁,只有胜之一人在那张猩红的织锦舞筵当中,如一枝风中的杨柳,飘拂宛转。在轻柔而节奏多变的音乐中,胜之下腰了,那头上斜插的金钗几乎擦到舞筵上;她穿的那种连兜肚也隐约可见的轻薄舞衣,把那苗条婀娜的腰身,勾勒得多么轻灵而撩拨人心。徐君猷对胜之这 《柘枝》舞,几可以说百看不厌;看时,必令他神迷魂销。不过,他此刻并未留意于歌舞。他在想,去年冬天,这雪堂刚落成之际,他也曾带着胜之到这里凑过一番热闹,可苏子瞻远无今天这般兴致。他在“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之前,心不在焉,只顾呵手去镊他颏下的几根白胡子。第二天,他专为这次兴会所作五首连章体《浣溪纱》中,有三首都写的麦苗、雪花一应庄稼农事,颇令人意外。而今天,苏子瞻竟判若两人,亦不得不令他意外。
舞蹈进入高潮,两条莲藕般匀圆纤长的玉腿在舞裙下闪烁。一阵急骤的旋转之后,人像雕像一般凝固不动了,两只纤手把那条轻柔的罗带提起来,袒开了莹白温润的酥胸,一双百媚横生的杏眼光波荡漾,直向苏轼飞去。乐声嘎然而止,苏轼如梦中惊醒一般,端起一满杯酒走到胜之跟前。胜之娇嗔地推着杯,苏轼一把钳住她的玉腕,硬把那杯酒从那樱唇中灌了进去;然后,当场赠给她一首《西江月》。顿时,把胜之高兴得两颊飞红。她跟乐伎们小声商量了几句,站到苏轼座旁,启开她娇莺宛啭的歌喉,为他唱了这首《西江月》,乐得苏轼呵呵大笑,捏住胜之的手久久不放。
饮酒作乐进行到深夜,苏轼自然大醉了。古人云:举杯消愁愁更愁。苏子瞻刚在生死边缘徘徊了一回,本不该如此敞怀大笑呵。徐君猷从席前站起,走到那张竹榻前去。苏轼在榻上挺身而卧。他比七月间消瘦多了,不过,脸色已显得白,眉舒目展的,恬然而安详。如果赤壁夜游那天,苏轼是因忧愁多喝了酒,那么今天,他明明是因快乐而畅饮。不过,那《赤壁赋》中的失意、忧伤和痛苦,飞到哪里去了呢?他那么倾慕庄周的返朴归真之乐,又何以如此沉溺酒色呢?这难道是在掩藏着更大的痛苦,或是对痛苦已经麻木?徐君猷感到不得要领。几个乐伎在座上打磕睡,他吩咐把酒席撤了。不料,苏轼竟已酒醒了,他霍地跳下竹榻,跟上木屐,连声呼喊苏迈,赶快备好文房四宝,他要写字了。苏轼要写字,这自然使徐君猷很感兴趣。苏轼素恶别人求字,至亲好友,倘主动求字,便片纸也不给,然而,兴之所至,则又非把纸墨写尽不可,田夫野老皆可得到。难得今 晚碰上这个好机会!徐君猷想。
苏轼颤巍巍在竹榻上寻到那顶短檐高筒帽,刚戴上头顶,忽然又一把抓下来,扔了。他在凉水盆里把半个脑袋浸了浸,撩起衣袖揩干。然后要了一大碗凉水,咕噜咕噜灌下去。这时,纸笔墨砚均已准备停当。他来到书案前,把那只笔筒抱过来挑笔。笔筒里的几支笔,还是熙宁七年他调离杭州时,向钱塘程奕专门订制的几百支中残留下来的。他挑好一支,用舌头舔了舔粘住的笔尖,蘸上墨,只略一凝神,便信笔书去。徐君猷特地站在苏轼的左首,以便欣赏他的用笔之趣。俄顷之间,苏轼那支笔如风行水上一般,潇洒自如,在那纸上留下衣片墨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写到哪里,徐君猷便小声地念到哪里。念到后面,他对苏轼那傲岸磅礴、如万壑流泉般神逸的书法,已全不在意,而被这首《念奴娇》所展现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境界,震惊了:几百年来,依声填词,谁人道出过此番境界?真是扫却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倘是关西大汉,执铁板而歌之,才真是一洗万古凡马空啊!
徐君猷被攫神摄魄般,在心中惊叹之时,苏轼已在词尾写好一段小跋。这跋二十来字,活脱脱画出一幅苏轼醉草图:
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
“君猷,这《赤壁怀古》填得如何?”苏轼把笔放了,转身向着徐君猷,面有得色地大声问道。
“很……”徐君猷正待叫出“好”字,却倏然记起苏轼在大青石上做的那个难以揣摩的梦:这首词,不正是他的那个梦吗?那天下
午,当他刚刚从梦境中醒来,便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周公瑾、曹孟德,他是何等留念着那个梦境啊!然而,游过赤壁,作了一篇《赤壁赋》,又为何把它一笔勾销呢?子瞻啊,子瞻!你心中崇拜、向往的“美人”究竟是谁呵?想到这里,徐君猷一把扭住苏轼,不容分说把他拖出雪堂,去到黑暗无人处。
“子瞻,你谁我呵!”
“嘻!太守醉了?”苏轼又是一脸顽皮的笑。
“你说,你明明仰慕周瑜,为何又要学那庄周,竟要驾舟浮海而去?”
“哈……”
苏轼仰天爆发一阵大笑,惊起雪堂前边那株孤高的悟桐上栖宿的鸟雀,喳喳喳飞向明月初起的天边去了。
“君猷,你看那天边,有什么?”
一弯娥眉似的新月,正从几片白絮似的云朵中穿出来,撒下缕缕柔辉。
“无非新月云彩而已。”
“再看看,这月亮和云彩动不动?”
“当然动。”徐君猷显得不耐烦了。
“月亮动?还是云彩动?”
“月亮穿行在云彩中。”
“哈!云彩不动?”
“……云彩也动。”徐君猷醒悟自相矛盾了。
“究竟谁在动?”苏轼迅疾地发问。
“……”徐君猷给逼出一头汗珠。
“不是月动,不是云动,乃是太守心动!哈……”
苏轼直笑得浑身乱抖。笑罢,他一巴掌拍在徐君猷背上,惊起正在机锋中出神的徐君猷。然后缓声道:
“君不知,吾非公瑾,吾非庄周,吾乃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居士苏轼也!哈……”
“东坡居士?呵,哈……”徐君猷若有所悟似的,附和苏轼大笑起来。
那天晚上,在苏轼的提议下,他们各骑了一匹马,在月色中乘兴驱驰。那马竟驰到了赤壁矶下。两人对着大江,流连一番之后,便又上马。这时,夜色迷茫,月光如水。他们不觉来到一座溪桥边上,都觉有些倦意,便解鞍下马,曲臂作枕,在那草坪上稍事休息。忽地听见杜宇啭啼,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来。但见天已大亮,左右乱山簇拥,流水潺潺,恍然不辨天上人间也。
(原载于1984年《现代作家》)
- 上一篇:陌生的城市,熟悉的角落住着孤独的人
- 下一篇:历史成语故事经典译文-英语:望梅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