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云:“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这里“过度乃占”,说的是日月星辰运行过程中那些异常天象的占卜和预言,这是星占成立的重要原则。
传统的观念普遍认为,日食、月食乃至“过度”天象的出现,都是帝王失德、失政的原因所致,因此每当日月运行出现异常时,皇帝和执政大臣都要围绕当时的朝政加强自身的修省活动。在这之中,修德和修政就成为帝王政治中最为关键的补救措施。
通常而言,修德主要指皇帝日常行为的自我规范和约束,而修政则是非常时期君臣对于朝政所采取的建设性措施。在帝王政治中,皇帝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人物,所以他的自我修省势必要对当时朝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围绕“德”与“政”的中心环节,帝王表现出的各种行为以及朝廷采取的各种及时应对措施,成为日食影响政治的重要内容。

1、
《乙巳占》云:“日蚀,则失德之国亡。日蚀,则王者修德。修德之礼,重于责躬。是故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这就是说,日食的出现常与国家的失德与灭亡联系起来。因此,日食发生后,帝王通常要进行攘灾的修德活动。而在修德之礼中,最为重要的是“责躬”,也就是皇帝自身行为的检讨和规范,实际上属于帝王“罪己”的重要范畴。
开元七年(719)五月日食出现后,玄宗“素服以侯变,徹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这里“素服、徹乐、减膳”,即帝王“责躬”的修德活动。在救护日食的诸多途径中,帝王的修德无疑居于最高层次。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日食在春分过后而未接近夏至出现时,文武百官要身着素服,而君主则撤去丰盛的宴会,并辟移正寝以等待日食尽早消失。这样看来,日食发生后君主避殿、减膳等的修省活动,在春秋时期已经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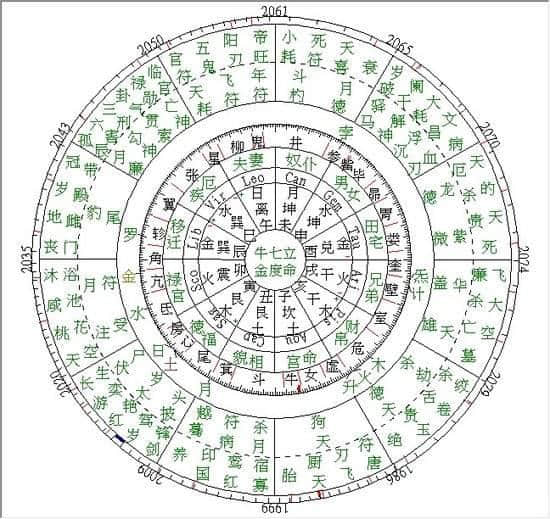
元和三年(808)七月,宪宗问宰相李吉甫说,昨日司天台预报太阳亏缺,结果非常准确,既然如此,那么“素服救日”又有什么意义?李吉甫回答说,日食因为是“自然常数可以退步”,太阳的运行具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所以日食的发生是可以推算和预测的。
但是他又说“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缓有急,即日为之迟速。稍逾常度,为月所掩,即阴浸于阳。亦犹人君行或失中,应感所致。”
李吉甫说,太阳运行的快慢是与君主德行的缓急始终相一致的。君主的德行一旦“失中”而违反常规,那么与此相应,太阳的运行也“稍逾常度”,进而为太阴所侵,日食接着就发生了。这时君主若能“素服而修六官之职”,加强自己的德行修养,“乾恭兢惕”,敬奉天道,灾祸自然就消失了。

基于这样的逻辑,日食出现后唐帝王加强自身修省活动的情况十分普遍。乾符三年(876)九月,日食发生后,禧宗“避正殿”以示修省。开平五年(911)正月日食,后梁太祖“素服,避正殿”,命令文武百官“各守本司”,暂时中止行政办公事务,同时颁布赦宥罪犯的诏书,通过这些方式“以答天谴”,减少日食带来的灾祸。
其实,皇帝的修德活动并不限于日食发生以后。由于天文历法的一长足发展,太史局(司天台)的日食预报较前而言更为准确。因此,每当国家的天文官员做出日食预报后,皇帝就开始实行“避正殿,降常服”的修省活动了。
开元十三年(725)十二月,玄宗封禅泰山结束,在返回“梁、宋”之间的途中,太史预报“于历当蚀太半”,于是玄宗“徹鳝,不举乐,不盖,素服”,但是日食并没有发生。
通常来说,日食出现时太史局都要提前进行观测和奏报,由此推想,帝王“罪己”的修德活动,更多的情况发生在日食之前。而且从“据旧章”来看,帝王素服、避正殿等的活动由来己久,至唐代早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修德制度。

2、
日食出现后,帝王除自身行为进行检讨和规范外,还特别重视朝政的建设。天授三年(692)“四月丙中朔,日有食之。大赦,改元如意。”可知武后改元,采用如意年号,实与日食的出现有关。至于大赦,旧书本纪称:“禁断天下屠杀”,当是日食出现后则天大赦的主要内容。
开元七年五月日食发生后,玄宗除了进行素服、徹乐、减膳的修省行为之外,还颁布诏书,命令中书门下两省审察囚犯,凡天下出现水旱灾害的地方,皆令贩济救恤,而对于一切“不急之务”,则全部停罢。
这些及时措施,由于针对了当时社会中的根本问题,所以从救护日食来说,应属于《史记·天官书》所言“修政”的范围。贞元九年(793)十月四日,司天监“言日食阴云不见”,文武百官纷纷上表以示庆贺,于是德宗颁布诏令,释放京师见禁囚徒。

《太平广记》卷92记载了一则由星变而引起玄宗大赦的事例:一行幼年家贫,邻居王姥前后救济数十万,一行常思报答。开元年间,一行得到玄宗的非凡厚爱,儿乎言无不可。适逢王姥的儿子犯了杀人罪,王姥请求一行予以搭救。一行遂用法术将北斗七星变为七头小猪藏在瓮中,致使玄象显灾,北斗七星不见于天空。玄宗因此大惊,急忙向一行讨求攘灾之法。一行请求玄宗大赦天下,于是王姥之子得以获释,而北斗七星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这则故事来源于笔记小说,更多的是民间的奇闻异说。不过,故事中一行所谓“今帝车不见,天将大警于陛下也”以及“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的议论,却有一定的真实性和普遍意义。既然北斗不见是上天对皇帝的一种警示,那么日食的出现则是更为严重的警示了,而帝王宣布大赦也是不难理解得了。
日食发生后皇帝的大赦除释放囚徒和禁止屠杀外,还要进行诸如减免赋税、赈济贫弱以及赏赐官吏等修政措施。开成元年(836)正月日食,文宗颁布大赦诏书,免除太和五年以前“逋负”以及本年京畿的“岁税”,并“赐文武官阶、爵”,不仅如此,此次开成年号的采用,也是日食出现的直接结果。
当然,日食发生后帝王对于政治的关注并不限于以上这些,比如开平五年(911)太祖除降赦有诏外,还颁布了日食求言诏书,援引汉代故事,要求文武百官上书言事,“列辟群臣,危言正谏”,以此来弥补朝廷政治的过失。不过,总体看来,唐代帝王因为日食而颁布的诏令并不多见,至于日食求言诏书,现有史料仅此一例。

3、
如果仔细追究,日食的发生还对帝王政治中的朔望朝会产生影响。《礼记·曾子问》记曾子向孔子请教朝会之礼,孔子说:“天子崩,大庙火,日食,后夫人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孔子将日食与天子崩,大庙火等联系起来,可见日食实是极大凶祸,一旦这类事情发生,朝廷通常要罢废朝会之礼。以后日食废朝就作为礼仪故事而被延续了下来,至李唐也是如此。
开元二十二年(734)闰十一月发生日食,玄宗诏救停止朝会。第二天日食过后,玄宗在应天楼接受了百官公卿的朝贺活动。“贞元六年正月,司天台预测癸卯朔日将有日食发生,于是德宗遂“停朝会”。八年十一月日食出现后,德宗“不视朝”。十年三月,司天台预报四月癸卯朔日食发生,太常博士姜公辅上奏说,“准开元礼,太阳亏,皇帝不视事,其朝会合停。”’
所谓“不视事”意味着皇帝不必亲临宣政殿,文武百官也不上朝参议政事。穆宗长庆二年)822三月,大礼院上奏说,“四月一日太阳亏,准开元礼,其日废务,皇帝不视事”。我们知道,历法中关于日食的推算结、果,通常情况下都在朔日发生,这势必要与唐代每月定期的朔望朝参制度相矛盾。

中唐以后,当司天台的日食预报与朔日朝会发生冲突时,唐王朝通常都取消了定期的朝会议政活动。不仅如此,日食发生时,皇帝一反常态,不处理政事,百官也各守本司,朝廷暂时中止正常的行政办公事务。这说明唐王朝对日食的预报和发生仍然十分重视,在此过程中,观察天文的司天台和以《大唐开元礼》为维系的太常卿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日食的发生还对当时的祭祀礼仪也有影响。肃宗元年建丑月(761),祠部上奏,请求“来年建寅月一日”举行祭祀昊天上帝的祈谷大典。但司天台却预报说,来年祈谷当天“太阳亏”,将有日食现象发生。于是礼仪使于休烈奏,认为日食时节举行祭祀大典,颇有不宜,应该选择其他时日,以与日食不相冲突,得到了肃宗的同意。
但是,根据唐代的日食观测记录,司天台预报“来年寅月”的日食并没有发生,因此计划中的祈谷大典是否另择时日,还有疑问。不过,从唐代举行祭祀昊天上帝的礼仪程序来看,朝廷要提前七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如此看来,由于司天台日食预报的错误,使得国家的祭祀大典向后推延也是必然的了。
日食的发生还对当时的军事战争具有影响。由于天象的观测一直是古代兵法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在唐代的军事著作——《太白阴经》中我们看到,日食的发生常常具有预测军事胜负的功能。后晋天福二年(937),司天台预奏说,“正月二日,太阳亏食,宜避正殿,开诸营门,盖藏兵器,半月不宜用兵。”。盖兵法著作中,日食的发生,无论对于军事出征以及战争的正常进行都有诸多不利因素,因此司天台建议,日食出现以后的半月之内都不能进行有关军事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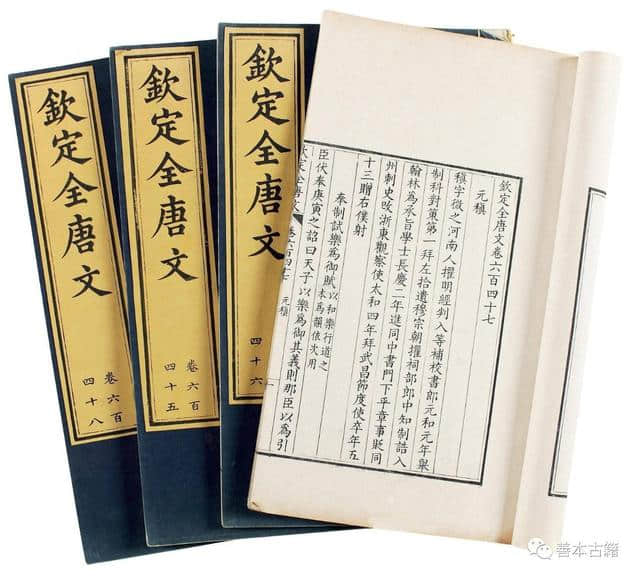
4、
日食的发生还对宰辅大臣的政治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全唐文》卷255苏颋《太阳亏为宰臣乞退表》文中“伏惟应天神龙皇帝陛下光被四海”云云,说明《乞退表》作于中宗神龙年间,当是神龙年间苏颧担任中书舍人时代替宰相而写的乞退状文。
根据两唐书《天文志》的记载,中宗神龙年间只有神龙三年六月丁卯发生过一次日食。如此,苏颧《乞退表》应作于神龙三年(707),而表文中“今月朔旦”当为六月丁卯了。
这次日食出现后,中宗“启辍朝之典”,下令诏停朔日朝会。“有司尊伐社之义”,说明文武百官还举行了救护日食的礼仪活动。除此之外,中宗“矜而有之,未致于理”,还颁布了释放与疏理囚徒的诏书。毫无疑问,这些活动都是李唐救护日食的具体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表文中“辰弗次舍,必贻上公之贵”、“胡广罢位”、“徐防免官”,所指其实都是汉代日食策免三公的情况。事实上,因日食而追究大臣责任,三公因此被杀者并不少见。如《汉书》所载,第一个因日食被杀的大臣是司马迁的外甥、宰相杨敞之子杨晖,以后丞相翟方进也因星变而自杀。

到了东汉,由于“权归台阁”,“机事转委尚书”,三公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于是因日食而罢免二公的事就成了常例。
传统的观念认为,日食的发生是阴阳失调,阴气侵阳的必然结果,而太尉、司徒、司空又以调和一!阴阳为其主要职责,于是追究责任,三公自然首当其冲。因而日食发生后,皇帝罢免三公就成为朝廷消灾弧祸的重要方式。
正因为如此,苏颋认为这次日食的发生,作为百官之长的“端揆”,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上表,请求皇帝“收其印缓,赐以骸骨”。应该说,大臣乞退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告老还乡、光宗耀祖似乎成为封建官员的一般归宿。但是,因为日食而乞退却有着另外的思想和政治背景,远不能与“赐以骸屑,”等而视之。
按照“天人合一”的普遍观念,日食的出现固然是皇帝失德的原因所致,但实际上也与朝廷的“失政”具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汉代三公“理阴阳”的职责仍然适用于唐代的宰辅大臣,日食作为阴阳失调的产物,同样与宰臣政事的失职联系了起来。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宰臣的逊位、罢职就成为他们调和阴阳、消灾饵祸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日食的出现不仅对帝王的行为有所规范约束,而且对宰辅大臣的尽职尽责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来稿/赵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