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2月5日,红极一时的大仲马在第厄普市附近的小仲马家里溘然长逝,告别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晚年生活。大仲马生前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浪漫主义作品风靡整个法国,甚至蔓延至全世界,但主流文学却认为大仲马仅是一个通俗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位置。直到大仲马诞辰200周年(2002年),仿佛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法国人做出了非常之举——把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享受和雨果同样的待遇,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

大仲马。
历史早已证明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然而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如《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在世界上却一直拥有大量读者,显示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他的小说大多放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下,故事性强,而且通俗易懂,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同时也迎合了我国二十世纪初提倡白话文的风气,所以相比其他外国作家,大仲马在中国格外受到欢迎。
《三个火枪手》最早被译为《侠隐记》
《三个火枪手》于1843年3月至1844年7月在巴黎《世纪报》上连载,1844年正式出版,小说以法国波旁王朝拉罗舍尔围城战为背景,讲述了以主人公达达尼昂为首的火枪手们为了维护王后的名誉,突破重重障碍,挫败黎塞留离间阴谋的故事。大仲马通过一连串的活动和生动个性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使整部小说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对话,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也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法国宫廷中的腐朽生活和统治阶级人物之间的伪善关系。
《三个火枪手》连载期间,在法国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大仲马也凭借此书开始声名显赫。此后《三个火枪手》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到国外。
我国最早的译本为光绪年间的伍光建译本。伍光建是与严复、林纾鼎足而立的翻译家,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07年,他根据英译本转译此书,并多有删节,取三位主角均为隐名侠士之意,将书名译为《侠隐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15年10月已再版三次。

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
茅盾在谈起伍光建的这个译本时赞不绝口。1924年4月,茅盾亲自为这两本译作校注,并写有《大仲马评传》编在卷首,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森然在《严复先生评传》一文中谈到伍译《侠隐记》时称其“可作为白话翻译品之代表”。
当时此书影响极大,不仅受到《新青年》的褒扬,还被教育部列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此后商务印书馆又于1927年1月、1930年4月、1932年10月、1947年3月多次重印。1982年和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分别高达328301册和341300册。
1999年,吴岳添编选的《大仲马精选集》将伍光建译的《侠隐记》收录在内。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也曾说:“在所有关于大仲马的译著中,最出色和最具影响力的是署名‘君朔’的老翻译家伍光建译出的《侠隐记》与《续侠隐记》”。

伍光建翻译的《续侠隐记》。
除了伍氏《侠隐记》之外,《三个火枪手》还曾多次被翻译和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以下版本:

《侠隐记》(曾孟浦译,启明书局,1936年5月。1940年1月再版)

《三个火枪手》(李青崖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三剑客》(许约翰、杨沈旦 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
《三个火枪手》(赦•瓦齐尔巴图 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三剑客》(罗国林,王学文 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11月)
《三剑客》(杨华,杜军 译,海天出版社,200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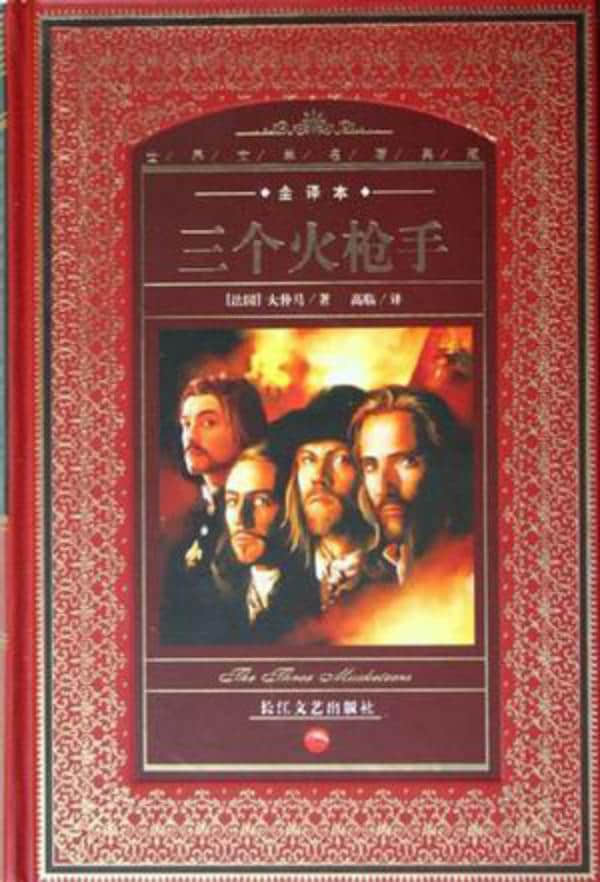
《三个火枪手》(高临 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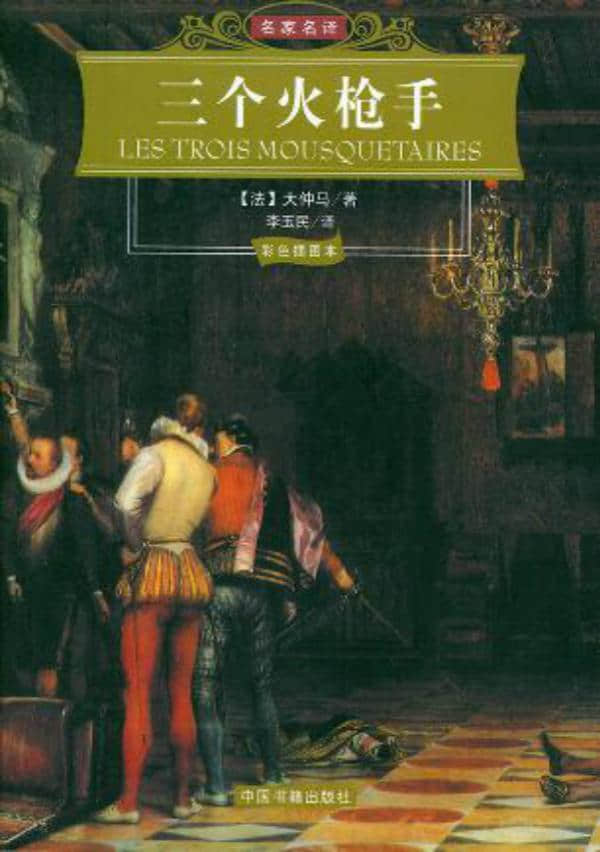
《三个火枪手》(李玉民 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5月)
最初被作为“政治小说”的《基督山伯爵》
《三个火枪手》出版不久,大仲马就写成了《基督山伯爵》,这段时间几乎是其创作生涯的巅峰期。故事以拿破仑“百日王朝”为背景,讲述了青年水手埃德蒙•唐泰斯因遭到诬陷入狱,越狱后得到一大笔财产并且改名换姓为基督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这部小说情节跌宕曲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大仲马充分利用自己写作剧本的经验,将一幕幕场景放到特定的地点,并以舞台的形式展开,由此形成的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巧妙的悬念设置成为本书的最大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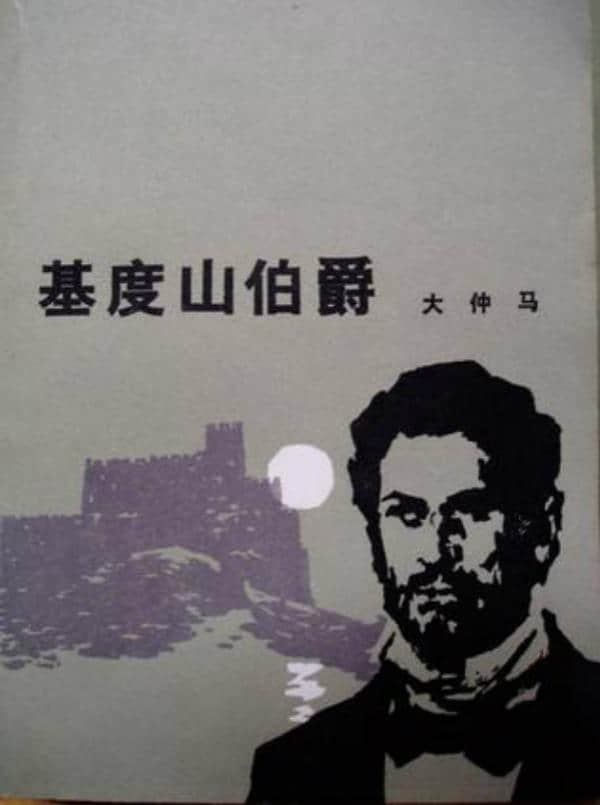
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2008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蒋学模先生病逝,各大媒体都将其作为“《基督山伯爵》最早的翻译者”报道了这一消息。实则,早在光绪年间就出现了第一部《基督山伯爵》的中译本——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甘作霖翻译的《炼才炉》。译文用文言行文,无标点符号,共计二万八千字左右。然而,此译本写到主人公唐泰斯成功越狱、获得宝藏就截止了,作为原著主体的“复仇”,却舍而不译。译者在序言里也解释了翻译的动因:“第为之揭其要旨,而定名为炼才炉,以谂观者。庶几我国之志士仁人,相与借鉴于斯。资为法戒,无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奋焉。” 由此可见,第一部《基督山伯爵》是作为“政治小说”推出的,旨在告诫国内志士,要卧薪尝胆,苦练成才。
随后出现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是1907至1908年在香港《中国日报》上连载的《几道山恩仇记》。1907年9月9日 报纸载:《几道山恩仇记》(上编),法国亚历山大仲马著、香港中国日报译。 9月16日 所载译者变成“香港中国日报抱器室主译”。此译本为全译,内容与英文全译本非常接近。而且,这部连载小说有单行本留传。然而,《中国报纸》是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创办的革命报纸,理应刊载革命小说,据此推断《几道山恩仇记》当时刊载于《中国日报》多少具有政治教育的目的。
而传统认为《基督山伯爵》的最早译本,则是蒋学模先生于1946年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我们目前读到的,大多是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书名已经改为《基督山伯爵》,分上下两册。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蒋先生首先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和创作历程,而后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粗浅看法”,包括大仲马“叙述故事的卓越技巧”。他认为这部小说“没有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的事件来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

《基度山恩仇记》改编的小人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
此后,随着《基督山伯爵》在中国的风行,此书的版本不胜枚举,此处从简列举相关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金庸写武侠或受大仲马启发
大仲马的作品以传奇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语言形式为载体,把历史事实与自然奇观融合起来,呈现出一种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20世纪初,这种另类的浪漫主义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西方通俗小说的大量译介,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实际上,大仲马的小说不仅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而且对一些作家和学者也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
作家余华在接受《北京晚报》编辑之约为读者荐书时说“这是我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书,去年我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首先为他选择的就是《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今年八月在上海时,李小林告诉我,她十岁的时候,巴金最先让她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大仲马的这两部小说”。余华还认为:“这两部巨著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
大仲马热爱历史,但并不为历史所束缚。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挂小说的一颗钉子”,他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的历史当中升华出艺术。在艺术与历史相结合的这一方面,金庸显然是受了大仲马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金庸的作品误解为对大仲马的抄袭。然而,金庸也曾不止一次表示过,自己对大仲马的喜爱并且受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坦言:“《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小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一三岁时开始喜欢,直至如今,从不变心。”
时至今日,大仲马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仍然备受推崇,他的小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相反被改编成多种影视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大放异彩。正如《大仲马传》的作者安・莫洛亚所说:“关于一部作品的价值,一代人可能自欺。四五代人,五大洲的人民是不会受骗的。……好脾气的仲马怀着赤子之心,通过他的英雄人物表现了自己的个性,适应了人们对于戏剧性和仁爱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是必不可少的,不分时代和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