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留下这样的遗书之后,王国维在1927年6月2日早上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沉思。大约十一时,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时已气绝。
今年是王国维诞辰140周年与逝世90周年纪念。生前,王国维被梁启超看作“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死后,郭沫若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而这样一位国学大师的自杀,更是成为了20世纪文化界最大的公案之一。
是“殉清”、“殉文化”,还是另有原因?在追思王国维时,人们对此产生了诸多解释或猜测。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认为他是“殉清”,当时北京的《顺天时报》也称他“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陈寅恪的说法则是“殉文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认为,王国维在理性上不赞成溥仪依托日本组织伪满洲国,但对溥仪又有师生情谊,在智与情矛盾的痛苦中,“看得破,忍不过”,终于在北伐军攻城之前选择了自杀;而以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为代表的“逼债说”称,由于王国维欠下罗振玉巨额债务,无力偿还,因此选择了死亡……
近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举办的“纪念王国维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学研究院教授刘东阐释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杀的最新理解。他指出,就算外在的成因都可以成立,这些偶发的诱因也只有通过一个关键性的内因,才能起到“一锤定音、无可挽回”的作用,而这个关键内因,正是王国维从青年时代便持有的悲剧观念。
而王国维的悲剧观,则要从叔本华的哲学说起。
叔本华、《红楼梦》,与王国维的悲剧观
王国维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并把金石、考据、绘画、书法等著作当作“课外书”阅读,年龄稍长,又跟随一位对西学颇有钻研的名师学习。在甲午战争到来之前,王国维已经是 “海宁四才子”之首,可是,他热衷新学而对科举毫无兴趣,于是在22岁时只身去了上海,到当时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就职。也正是在上海,他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哲学思想,并被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深深感染。

叔本华认为“生命因意志而存在,现实中意志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生就是痛苦的”。受他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只有知苦痛才能奋起,才能避免麻木”。1904年,从日本短暂留学回国后,立志要从事于哲学研究的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了《红楼梦》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首先讨论了生活与欲望的关系,他把宝玉、黛玉、妙玉、红玉、玉钏等人名中的“玉”字解释为 “生活之欲”,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厌倦,人生就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摇摆。而欲望、生活与苦痛,三者实为一体。
既然生活本身是欲望与痛苦,王国维便把艺术当作逃避现实的乌托邦,使人忘记物我之关系、忘记生活之苦痛。而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更能够发挥乌托邦的作用。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依照叔本华的分类,王国维把悲剧分为三种,一是恶人作祟,二是盲目的运命,三是悲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而《红楼梦》属于第三种也即最高层次的悲剧,它与传统文学中常见的盲目的乐天精神和大团圆结局相悖,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刘东称,在中国的乐天倾向和西方悲剧精神对比下,王国维态度决绝地作了优劣断定,使得本来未显得如此高明和重要的小说《红楼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越古代诗文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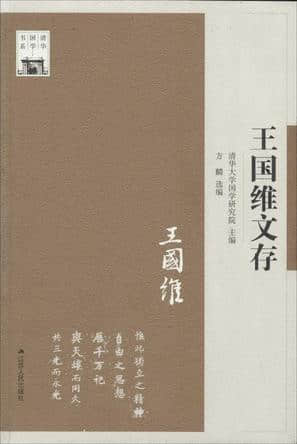
王国维还认为“解脱”是伦理学上的最高理想,他提出,中国文学中真正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只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它们的主人公或死或散,触及了人生的真正苦痛。《桃花扇》主要是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非以描写人生为要务。而且主人公经历沧桑之变,不能自悟,而要以道士之言才能醒悟,所以它的解脱是“他律”的解脱。而《红楼梦》的解脱才是“自律”的。它的主旨是“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这也是《红楼梦》较《桃花扇》的高明之处。在叔本华看来,一个“解脱”的人“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在解脱之后,我们面前就仅仅是个空无。王国维对此深信不疑,并把《红楼梦》中“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当作是解脱之境的具体化。

《红楼梦评论》将《红楼梦》一书完全套入叔本华哲学理论当中,其中不免有牵强,比如王国维把“九十八回”以后黛玉之死至宝玉出家奉为全书精华,是“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但这里却通常被认为是全书的败笔。尽管如此,《红楼梦评论》依然是“红学”研究绕不过去的著作。王国维对《红楼梦》这一“悲剧中之悲剧”的定位,奠定了中国乃至世界“红学”研究的基调,随后所有的评论都将《红楼梦》纳入到悲剧之列。
刘东认为,《红楼梦评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新红学”的诞生、美学学科的引入乃至比较文学的发端,甚至还在现代中国造成了暗中抱持和普遍秉有的理念:凡是对人生达到了悲观判定的作家,就总要比对世界还抱有乐观态度的作家更为深刻,也显得对他所属的社会更负责任。在现代文学的官方名人堂中,“鲁、郭、茅、巴、老、曹”被认定为“成就最高”的作品,都是广义上的悲剧。可见,王国维这篇万余字文章,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同时成为了许多领域的开山。
尽管已经认定了“人之大孽,在其有生”,但28岁的王国维还有很长的治学道路要走。在1912年,王国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著中抒发过的悲剧观念。在这本书中,王国维肯定了元杂剧的悲剧美,认为元悲剧中最有悲剧性质的是《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原因在于“其赴汤蹈火者,乃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这样,元杂剧就成为了一种能够与西方美学传统价值相比较抗衡的中国艺术传统。
然而,王国维对悲剧美学的信仰,却被叔本华的文字本身束缚了。
王国维,一个真诚的悲剧信徒
在王国维埋首于“以西格中”(即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方式解读中学)的研究时,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逆转,辛亥革命成功了,民众还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失去了依傍了两千多年的统治者——皇帝,对于一国的前途,一些人感到迷茫。在友人的帮助下,王国维和朋友罗振玉去往日本暂避风潮。
在日本,王国维“以其自觉而强烈的学术意识感到自己应该回归国学,为已经被纷乱新学搅扰得濒临破碎的堂堂国学尽一份中华学者之责”。(窦忠如著《王国维传》)因而“尽弃所学”,从此不再深究西学,投身国学研究。在十五年(1912-1927)时间里,他在经学、古文字学、训诂、声韵、名物、甲骨文和商代史、周代青铜器物与金文、周代制度、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演变、汉魏学术、魏蜀石经、汉晋简牍、唐人写卷、古代地理、宋代以来金石学、边疆近代新出碑铭、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史、西北史地等诸多领域有所创获。历史学家张广达称,“他的学术水准为他确立了国学祭酒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学界无分新派旧派的一致悦服和当代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崇敬”。
可是在刘东看来,王国维对西方学术率然的放弃,带来了相当消极和匪夷所思的恶果。正是因为王国维没有继续了解叔本华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转折或自省,才使得他一生都未能摆脱叔本华的阴影。
对于叔本华本人来说,把悲观观抬高到哲学层面不过是博取名声的手段——他的生活行为和他的哲学主张在种种方面都大相抵触:贪口腹、恋女色、畏死亡,甚至为了红尘俗名而雇用通讯员搜求自己声望的证据……很多人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叔本华对自己的论调也信得不真诚。(刘东:《叔本华:没有意志的意志哲学家》)
对悲剧推崇备至的胡适,也曾出于与王国维大体相同的理由高扬《红楼梦》的思想地位。但刘东认为,同叔本华类似,悲剧观念对于胡适这位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来说,顶多也不过就是些“嘴皮子功夫”,根本不会影响到他的高级生活质量。但和叔本华、胡适不同的是,这些观念被灌输到王国维心中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份量。

王国维曾为《静庵文集》续编写过一篇序文,自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即身体软弱而性情忧郁。旁人对王国维的印象则是“真诚笃实”,鲁迅就曾称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中》中记载,王国维“对人不很会讲应酬话,很不会客气”,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假使说是“靠不住的”,那人无论找出什么话,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还只是“靠不住的”四个字,不附和人,也不和人驳难。而他待人也极度真诚,在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皇宫被辟为故宫博物院时,王国维坚决不允许没收皇帝“私产”。刘东认为,正是由于王国维情感浓郁低徊、沉潜刚烈,在接受了叔本华的论调以后,就不仅限于说说而已了,正是对这种悲剧观的真心坚持,才让王国维走上了自沉昆明湖之路。
在刘东看来,王国维的自杀并非仅仅来源于个人天性或繁琐家事,而是凸显了二十世纪初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压强,以及在那种压强下不明就里的盲从。在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盲从当中,一度连“自杀”——尤其是“诗人自杀”——都被说成富于“意义”的,或者至少表达了真性情,因此也值得为之喝彩。这种对西式悲剧观的崇拜,在1980年代又被重新发现,海子等诗人的悲剧也一概都受到了追捧。刘东认为,这种消极弃世、自我毁灭的态度,是一种“蛮横无理”的人生解决方案,不具有哲学价值,也是不负责任的生命毁弃。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