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以回避的三个历史人物
——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与敦煌学的渊源
雒青之
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清晰了一门显学的容貌。敦煌学在曲折发展中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中国敦煌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笼罩在敦煌学上空的疑云迷雾,却久拂不去,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的评价问题已经使我们难以自噤——回避的时代已经结束,要么继续旧日经文的诵颂,要么进行深刻的反思,二者必具其一,因为以上三人是所谓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任何企图绕开他们侈谈敦煌学显然是徒劳无益的。这三个人的历史定位究竟如何?是像我们多年来乃至今天仍然坚持宣传的那样,是“卖国贼”、“强盗”、“骗子”,还是对敦煌学发展具有历史功绩的普通民众与著名学者?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后者。肩负十字架踽行敦煌学数十年的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我们进行敦煌学研究的梦魇。在学术理论上正本清源,匡误纠错,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学人起码的良知和勇气,这,也是笔者写作《百年敦煌》一书及本文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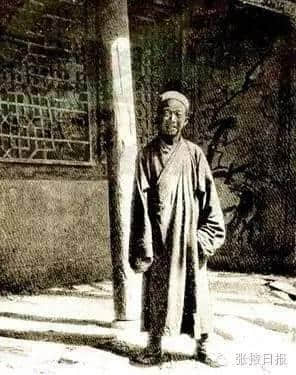
(王圆箓)
王道士何许人也?一介草民而已。他是陕南某山区人,祖籍湖北麻城。可能与战争、饥馑引起的流民迁徙有关。1899年,作为游民的王圆箓来到敦煌,开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王圆箓这个名字,是在他成为道士后改的。如果不是他于1900年偶然中发现了藏经洞,王圆箓这个草民姓名,决不会见于经传的。及至他处心积虑地用他认为是最满意的方式和斯坦因、伯希和做了交易,最终使石窟藏书的精华部分流落国外后,落在他身上的罪名也就难以洗刷干净。人们不假思索地一言以蔽之曰:“勾结外国强盗的卖国贼”。特别是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即斯坦因、伯希和与王圆箓交易的性质;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许多人并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得出说服人的结论。因此,笔者在其拙作《百年敦煌》中探讨了这些基本观点。
关于藏经洞交易的性质问题,人们习惯上认为,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勾结外国强盗骗子,出卖国宝,遗罪千古。当年王圆箓和斯坦因、伯希和进行的交易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斯坦因用七百两白银,伯希和用五百两白银,换取了藏经洞里近二万件文物,连斯氏本人也毫不掩饰,认为确实便宜。可是,对于王圆箓来说,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反而很高兴,觉得买主颇为大方。因为在此之前,当他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物向地方官员“出卖”时,对方不是不识货,就是只拿东西不给分文。而对于王圆箓来说,需要筹措钱款维修莫高窟和实现他“宏扬佛法”的理想。关于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有人指出,王道士一没有权力出卖,二有义务去守护。他未能这样做,自然应以“监守自盗”论处。但坚持这个论点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藏经洞是“国家财产”;王道士是“法定”或“准法定”文物保管人员。问题是,这两个基本条件存在不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的寺院在历代皇权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而且伴生出独特的寺院经济。寺院田地可以免缴赋税,可以出租,寺院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连皇帝都要给著名寺院“进贡”。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皇室供奉珍品之事,足以证明。
王圆箓身为莫高窟实际意义的“掌门人”,只有他有权掌管藏经洞的钥匙。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并没有“爱国主义”或“卖国主义”的头脑。只所以最后与外国人成交,是因为外国人掏了银子,不象官家只想白拿。作为官府,也自始至终没有把那一洞子佛经占了绝大数量的文物视为“国家财产”。1900年王圆箓初次打开藏经洞后,就用毛驴驮了两箱经卷去见安肃道台挺栋,这位官人看了两卷,就说古人的毛笔字还没有他写得好,使王道士碰了一鼻子灰。1902年,湖南进士汪宗翰任敦煌县令,得到了王圆箓送的卷子后很感兴趣,遂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学识好,爱金石,又适逢编订《语石》一书,了解到藏经洞情形后,托汪宗翰“代求”了一些卷子以备出书之用。一直到1910年,藏经洞下余卷子才辗转运抵京师学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斯坦因第一次离开千佛洞时,拉了五牛车卷子,地方政府并没有干涉,相反是“得地方官之允许”。第二次从藏经洞购得十二大箱文物后,为了先去其他地方考察,他竞将这些东西“安安全全地寄放在安西县衙门里”,1910年下余藏经洞文物解往北京时,清廷学部曾给千佛洞寺院“补偿”了一笔钱。从“补偿”而非“赐赏”来看,清廷也承认藏经洞文物乃为寺院所有。连叶昌炽编书需用的卷子,也是托汪宗翰“代求”的。求谁?自然是王圆箓了。可见藏经洞文物归寺院所属确凿无疑。
既然藏经洞文物不是“国有资产”,王圆箓又不曾拿官府俸禄充当保管员,就不存在“盗卖”、“监守自盗”之说了,问题本来就极简单,王圆箓既没有保护文物的法律责任,也没有“无私贡献”的义务,他是出家人,世俗的道德难以约束他。
王圆箓一辈子都在为恢复莫高窟昔日的荣耀做不懈的努力。他参与或直接完成了“九层楼”、“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建筑的修建。补葺大小佛洞,建造厅堂客舍等寺内建筑,绿化寺外环境。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就是王圆箓扩建成的。王圆箓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成为特定事件的关键人物,既有历史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是王圆箓,而非别人发现了藏经洞,他从此就成了敦煌学研究链条中不可舍的一环。
王圆箓的历史功绩的实质是:凡经过他的手卖给外国的石窟遗书,至今没有一件毁损,全部静静在存放在国外的博物馆和科研单位里。而流失于国内的则绝大部分不复存在。当年藏经洞文物总数达五万件以上,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运走的不到一半,那么,其余的东西如今在哪里呢?君不见藏经洞“劫余”后剩下的千余件卷子,在宣统元年运抵京师时,被当时堪称“著名学者”兼朝廷大员的“四人帮”连偷带抢,做为私产,甚至把长卷一分为二,手段殆毒。
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的动荡年月里,适逢西方优秀的、卑劣的探险、考古者们,纷纷前往中亚腹地探宝之时,历史推出了一个并不愚昧的王道士,与职业道德及个人素质堪称当时一流人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相遇,实乃不幸中之大幸。由于这个历史的偶然性,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必然——敦煌学由此诞生!在被誉为二十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藏经洞的发现中,王道士永远是难以回避或排除的关键角色。是敦煌学产生的重要人物,从这个历史意义上讲,建立一个“王圆箓纪念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二
与王道士相会于敦煌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世界上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在中国,他们历来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强盗”、“骗子”、“间谍”。而在国外,他们的肖像高挂在学术殿堂的上方,他们的有关著作成为敦煌学研究的经典,他们的学术成就照亮了几代后学之士,他们的文化人格成为做学文者的楷模,两种评判,就如同川剧艺术里的“变脸”,何其差别乃尔!其实,只在认真翻阅一下斯、伯二氏的学术著作和有关传记,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一些判断何其差廖!
人们斥责斯坦因、伯希和,总认为他们就是“文化强盗”,劫掠走了国宝,盗走了地下文物,横行于中国西部,拍摄地形,干着不可告人的间谍探子活动,是品质恶劣的帝国主义分子。
实际上恰恰相反,斯坦因、伯希和是著名于世界的学者、考古探险家。著作等身,是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的奠基人。是西亚、中亚考古发掘的发现和保护者。他们拥有合法进入中国考古探险的护照,他们在西域的考古发掘严格遵从行业规矩和要求进行,是当时众多外国考古探险家中最具职业道德者。在考古、地理探险、东方语言学诸多领域内,他们分别取得了无人企及的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和旷世大师。
斯坦因、伯希和都是二十世纪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从小勤奋好学,并且学业有成。斯坦因先后攻读于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土宾根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伯希和毕业于法国现代东方语言学院,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汉语教授、法兰西学院特设讲座终身教授、法国亚洲学会主席、苏联科学通讯院院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斯坦因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次中亚考古探险,就是在这历时几十年的时间里,总计获得各类文物数万件,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有关收藏。那些包括藏经洞发现物在内的敦煌古代文物,以及内容翔实、范围广泛的敦煌学巨著,极大地丰富了中亚考古内涵,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使研究人员有可能从学术研究的荆棘中走向坦途。结合考古发掘,斯坦因利用其渊博的知识,准确认证了一些久已湮没于流沙的历史古迹。如中国史书所载“精绝国”;玄奘当年经过的“ 货货逻迹”,以及大名鼎鼎的“阳关”。
从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的实际观察,他是最有职业道德、最注意文物保护的学者之一。他的考古实践虽然采用多种方法,但从不采用本能使文物保存下来而去破坏的手段。他的考古方法符合考古工作的一般要求。如果告知那些一味指责斯坦因的人,斯氏发掘出来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那些珍贵的文字文书资料,竟然相当一部分是从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翻捡出来的,相信者肯定不多。人们总愿意把斯坦因和当代的揭墓贼联想在一起,以为他穿堂入室,然后一件件地拿走其中珍宝。孰不知,斯坦因每到一地,目光首先倾注于遗迹的垃圾堆。这是因为,经过当地“寻宝人”,亦即土生土长的文物盗贼的长期光临,容易得到的珍宝类文物大都丧失殆尽,而保存在古代垃圾堆里的文字文书以及织帛类遗存物,是任何“寻宝人”不屑一顾的。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德悦遗址、楼兰遗址,斯坦因和他雇佣的工人,长时间地在刺鼻的臭味中,翻捡几个世纪前的垃圾堆,寻找其中的遗存文物,得到了我们称之为“国宝”的东西,斯坦因堪称为“垃圾博士”。
在清理遗址,发掘古墓,割离、搬走壁画这些考古内容方面,斯坦因表现了一个有着良知的考古学家的理智。有的地方,他对清理出的壁画造像拍照后回填。有的地方,他只一铲下去,探明文化层的关系即可。而有的地方,则需要做永久性剥离搬迁,如坍塌的寺庙,“寻宝人”劫掠一空的墓室、自然力下即将毁灭的遗迹等。抢救性措施可能是保存这些遗存物的唯一办法。有些人对于中国的文物放在外国总是想不通,但是如果对他说不这样做这些文物早就消失,他们反而坦然。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吗?
斯坦因的地理考古与探测也极具水准。通过艰难的地理勘探,斯坦因解决了其考古探险中一系列疑难之点。他沿途拍摄的山川风土人情民俗照片,生动高雅,为其著作增辉不少,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那种认为斯坦因可能负有某种“间谍”任务的观点,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臆想而已。
斯坦因身为著名学者、专家,其个人品行素质、在其对从事的科学工作的责任意识和献身精神上,中外学术界有口皆碑,无不予以高度评价。从兴都库什至帕米尔,从昆仑山到罗布泊,从废弃了的古丝绸之路到风沙掩埋了的长城烽燧,斯坦因一步步走了过来。在高山雪地,他曾冻掉了几个足趾。在罗布泊沙漠,他差一点命丧沙漠。在吐鲁蕃,他遭遇携带枪支的强盗。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1943年,八十一岁的斯坦因获准进入他盼望已久的阿富汗去考古探险,却中风逝于喀布尔。根据本人遗愿,斯坦因遗体被安葬于喀布尔公墓。当时,阿富汗、美、英、波斯、伊拉克、苏联及许多国家驻阿代表参加了斯坦因葬礼,表示了对其的敬重。
斯坦因一生勤于著书立说,他的关于中亚的考证报告与研究论著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敦煌学研究不可替代的珍贵原始资料,他是敦煌学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之一。
在敦煌学建立上同样有卓越功勋的,是斯坦因同时代、学术活动上的强有力竞争者法国学者伯希和。
如果说,斯坦因以其丰富的中亚考古资料和实物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的话,伯希和则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大师地位,以其对敦煌学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公认的“敦煌学之父”。
伯希和自幼便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语言天赋,尤其对东方语言具有罕见的兴趣和才能。他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东方语言天才,他精通古汉语、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安南语等数十种语言。
王道士和斯坦因的交易为伯希和的效仿铺平了道路。王道士只认马蹄银,尽管他丝毫不知道对方是多么杰出的学者。接过王道士递过的钥匙。伯希和秉烛三周,从斯坦因过了一手的石窟藏书中精选出经卷写本和少数民族文卷共计六千多件。可以说,藏经洞卷子里最有文物价值的,莫不被他搜罗而去。
1909年8月,伯希和将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带至北京“六国饭店”,并用一口流畅的汉语作了演讲。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参加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罗振玉相会伯希和并索要有关敦煌遗书资料,伯希和慨然相付,同时与之畅谈,据罗回忆二人相谈投机,以至于“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这就是罗振玉著述《敦煌石遗书》来由。之后,伯、罗二人关系日趋密切,学术交流频繁。从1910年至1913年期间,伯希和从法国源源不断地给这位相识不久的中国学者寄来了包括古典籍、地志、图经、星占书、阴阳书、古类书等敦煌写本的影照,这又形成了罗振玉的《鸣沙室佚书》。伯希和的虚怀若谷不仅于此,他还同时对其他求教的人在学术上给予帮助,包括中国学者王国维和日本著名敦煌学家羽田亨。中国敦煌学的萌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茁茁而生。首先是罗振玉、王国维和伯希和的个人交往,为中国敦煌学的萌芽提供了一块小小的园地。凭借这一块沃土,中国敦煌学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举世瞩目的境界。那些认为中国敦煌学是中国人白手起家,与“强盗”无关的看法,显然是不客观的。
除了国际学术交流外,伯希和在敦煌学领域内创造了若干个“第一”,成为和斯坦因并驾齐驱的西方敦煌学研究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同时代所有敦煌学家。伯希和是最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编号的人,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编号目前在敦煌学研究中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参照。他是最早对莫高窟进行系统、大规模摄影记录的人。其结果是六卷本《敦煌石窟》的大型画册问世。在东、西方,这个画册成为启迪、研究敦煌学的钥匙。常书鸿走上敦煌,据他自己讲,就是从巴黎街头书摊一册《敦煌石窟》画册引发的。现敦煌研究院一些老研究人员,也承认自己从伯希和有关著述中受益非浅。伯希和又是最早研究敦煌写本的人。1911年开始,他就开始就敦煌写本不断发表研究论文,其论文的价值举世共认。伯希和还是最早为敦煌写本编目编号的人。最后,他曾详尽地对莫高窟壁画中大量的题识、题款、榜题做了记录,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专著《笔记A》和《笔记B》。从伯希和A、B笔记中最大获益者是敦煌学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珍重这两部笔记的原因,是因为伯希和抄录下的题记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对洞窟壁画一个世纪来,由于天灾人祸和自然因素而造成的某些题记的损坏、剥落、消褪,引发研究困难时,尤其显得重要,它起了“孤本”校勘依据的作用。1994年,我国正式出版了伯希和AB笔记的译本,这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件盛事。
无论是斯坦因还是伯希和,敦煌的考古探险和敦煌学的研究,都只占他们一生中学术成就中的一小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却已使其他研究者难以企及。因此,无论身前身后,他们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敦煌学前驱人物罗振玉、王国维、蒋斧等人,他们对伯希和在学术研究上的帮助怀有深刻印象,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了敬意。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西亚、中亚考古探险热潮,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文化浪潮。精英人才聚集到这块广袤的沙漠戈壁上,凭借其才识进行了空前的竞争。处于最黑暗历史阶段的中国自然无法与其较量,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宝外流。今天,许多人从单纯的爱国主义情感出发,对斯坦因、伯和还有王道士予以遣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明了内情的学界人也这样讲就不妥了。诚然,除了精英外,当年来到西域的也有如美国的华尔纳、德国的勒考克之流,他们曾大肆破坏精美的壁画,成为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历史罪人。这些人在当时就遭到包括他们本国学人的唾弃,是不可混同于斯坦因、伯希和而论的。
当我们冷静的审视历史,回顾百年敦煌时,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王圆箓的发现,没有斯坦因、伯希和与之交易,就不可能有敦煌学这门学问。我们也不能不宽慰的是,历史老人将“极其狡猾机警”的王道士和品学堪称一流的斯坦因、伯希和“组和”了起来,在敦煌千佛洞里演出一场“悲喜剧”,最终使藏经洞文物中的精华部分安然无损地保留下来,成为不幸中的大幸。人们习惯于用现今的口号和原则去苛求古人,认为“应该如何如何”,这,不是太过于偏离现实吗?但如果绕过此三人,不谈他们的历史功绩,那不就成了最新版的“驼鸟政策”?因此,不论做什么学问,包括敦煌学,顶要紧的是事实求是的学术态度。

(作者近照)
(作者系甘肃张掖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内容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期编辑: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