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以来先觉者们的思想,现在阅读起来,往往给人一种那时的思想依然没有过时的感觉,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种感觉,虽然不无苦涩,却也让人惕醒思变。
《明夷待访录》有二十一章,犀利清透,毫不犹疑,针针见血。比如开篇《原君》就直斥一国之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再比如《原法》篇,揭露君主专制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原臣》篇则说国臣(国家干部)“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什么是“一姓”?虽有明面上的一姓与暗地里的一姓之别,但是,凡将天下与万民统驮于一家一派者,哪怕是以天下与万民之名义而行一家之实者,都可称为害天下的“一姓”。这是十七世纪中叶时,中国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峰,可谓中国民主思想的先声,比卢梭的《民约论》还早九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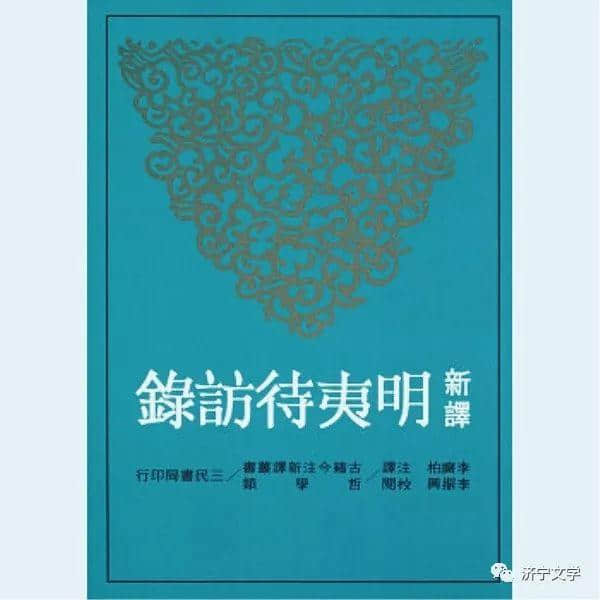
二十一篇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学校》篇。
《学校》篇说到天子一言九鼎的害处是混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而让学校成为一个善思考并敢于说话议论的地方,则可以抑制当权者的为所欲为,从而达到长治久安——“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君安而国可保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了学校议论风生的气候,“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反之,将学校中的畅所欲言,视之为“衰世之事”,甚而至于“收捕”发言者,则是亡国之兆。学校当然不仅是议论与批评,更主要的是培育与生发。培育与生发什么呢?“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就是培育生发一种从上到下的“诗书宽大之气”。读到这里,一种对诗书的渴念,一种对宽大之气的向往,就在胸间积攒聚集,恍若身在中国十七世纪黄宗羲的那个年代。黄宗羲同志真是不简单,在那样的明末清初,不为利诱所动,不为风云所惑,心系天下,心思变革,有胆有识,敢发世之先声,将沉默又沉闷的中国撬开了一条可以透进新风的裂缝。
黄宗羲活了八十五岁,早早地就处于人生的通透之中。如他的“四可死”,比那些死了还要让尸体在化学药物里“不腐”的国君们高明多了。民主与专制,普渡与万岁,一个死字即可见分晓。黄宗羲临终前四天给他的孙女婿万承勋写下一封四可死信,说“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他死去三百二十四年了,今天的我还在有滋有味地读他的书。
余英时先生说黄宗羲的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秦晖教授说黄宗羲“在民权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在这样的时代,不妨读读《明夷待访录》,挺有意思的。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