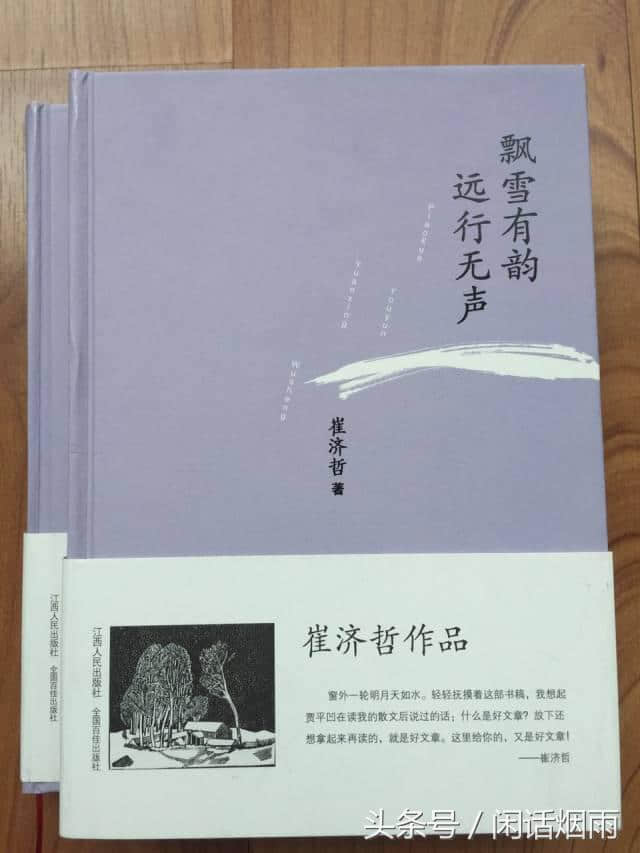文/白头翁
壹
壬辰秋上,去河北满城看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陵墓。刘胜的王陵是座没有被盗过的“原始”汉墓,着实珍贵。走进靖王陵,一切都是“原模原样”,“原汁原味”,那就是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诸侯王的生活。我惊讶地发现,在刘胜仓廪库房中,存放着一条条肉脯,竟然是鼠肉做成的肉脯、肉干。难道2000多年前,人们就把鼠肉送上了餐桌?西汉的王已经在宫中有滋有味地吃鼠肉了?中国西汉的风俗是视死如生,刘胜把他生前在宫中的一切生活享受都带到地下了,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西汉时期,至少在中山国,鼠肉已经是人们食品中的美味佳肴,否则它不会进入到王的食品库中。

据我考证,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吃的鼠肉当为田鼠肉,而不是我们说的仓鼠肉俗称耗子肉。
什么年代中国人不吃鼠肉,厌恶鼠类?没有查到史料文字的记载。有文字记载吃鼠的,似乎只有西汉时期的苏武,苏武在被匈奴放逐到北海边上,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放羊,用等公羊生了小羊才送他回汉朝来威胁和动摇他。苏武不为其所动,志坚如铁,他就依靠挖野菜和逮田鼠为食,而且为了生存,他是生啖活鼠的。苏武了不起,但他吃鼠是被迫不得已,但他毕竟吃过老鼠,且是常年吃。
唐代柳宗元有“永某氏之鼠”为证,别说吃鼠肉,见到老鼠都恶心,称之为“阴类恶物也”。于是“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如唐人食鼠,如丘之鼠,恐怕剥其皮可做鼠皮大衣,食之肉,恐怕亦有数百斤之多,“弃之隐处”,岂不惜哉?
到了明王朝时,蒲松龄写过一只大耗子,民间老话说快成精的耗子。蒲松龄在此篇中并非“神聊”,更不是编什么“狐狸精”、“耗子精”的故事。蒲松龄是用写实的手法在记述他听说的一件事,因为此事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皇宫内,蒲松龄不可能亲眼见,但他能亲耳听。万历年间皇宫中的这只大耗子真凶,个儿长得跟猫差不多,比猫凶得多,把宫中的猫都当猎物咬死当餐。此乃有文字记载中第一次记有耗子吃猫的记载。没办法,因为这只大耗子太闹腾,“为害甚剧”,又无“克星”,闹腾为害得日甚一日。恰巧有外国进贡的狮猫,这才演出一场精彩而激烈、智慧而残酷的猫鼠大战。其结果也让人惊心动魄。“猫即疾下,爪掬顶毛,口齕首领,辗转争持,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启扉急视,见鼠首已嚼碎矣。”要不是引进一只外国“狮猫”,这只宫中的大老鼠还不得把万历皇上的五脏六腑全吃了。

贰
鼠是高智商的动物。
明末崇祯年间,北方屡闹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老百姓只得吃“观音土”。农民懂得田鼠,为活命,常常举家去地里挖鼠洞,“抢”田鼠的口粮为生,谁知道田鼠洞几乎洞洞皆空,更让人难解的是赤地千里,竟然千里不见一鼠。老鼠早已“举族”逃难,搬迁远遁。
上世纪四十年代,豫中大旱、大饥,灾民扶老携幼上山下地,把能谋生的手段都用上了,从树叶、树皮、草根、野菜全部吃光以后,把能找到的昆虫、野兽、动物都吃进肚子,为活命,他们抓光了几乎一切动物,但没有人抓住过一只鼠类,不是人类无能,灾民早已饿红了眼,但鼠类似有预报,在大灾发生时,还没到吃它们的时候,它们就跑了,跑得无影无踪了。据说黄河发大水之前,村里连一只耗子都看不见,仿佛它们已经得到了凶讯。
有年半夜,摆渡撑船的老船工半夜醒来,听见河中仿佛有千军万马正渡河。慌得他连忙站到船头,借着月光往河里一看,吓得他差点一头栽进河里。原来河上正有数不尽的老鼠在渡河,一排排、一列列、一片片、一阵阵,数也数不尽,哪儿来的这么多老鼠?为什么有那么多老鼠要过河?他一个船工不知道,只好对着月亮合十祷告,求老天保佑。三天以后,河那边发生了地震,那就是邢台大地震。
行船中,船舱中有老鼠,据说有的连头带尾长达一尺有余,在船舱中常常大摇大摆,不慌不忙的“招摇过市”,别说船员连船长对耗子都毕恭毕敬。因为船舱里的老鼠对他们来说是福星,如果老鼠们在船舱中过的悠然自得、幸福美满,这就说明此船无碍,走你的吧。如果船舱之中的老鼠皆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尖叫逃窜甚至以头撞舱板,那这船危在旦夕,朝不保夕,大难临头。世世代代的船老大口口相传,百试不爽。老鼠有特异功能。
老鼠这“神物”也真了不得,它曾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李斯。《史记·李斯列传》中说:“李斯者,楚上蔡人氏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老鼠是李斯从政的启蒙先生。
我在新华通讯社山西分社当记者时,经常下煤矿,常在煤矿的井下工作面上看见贼眼闪耀的大老鼠,有的还三五成群。矿工们对它们也是不烦不厌,尤其在井下班中餐时,井下的老鼠会围上来,有的甚至会跳到矿工腿上讨吃的,矿工尤其是老矿工都高高兴兴和言悦色地喂它们,通常是老鼠和矿工一块进行班中餐,老鼠吃饱以后会自觉地蹲在矿工跟前,友好亲切地看着矿工们吃饭、喝汤、说笑。矿工们说,有老鼠在,咱就安全,如果有一天井下无鼠,矿工们会一溜烟一窝蜂地上井,井下已有安全隐患,很可能瓦斯、大水、冒顶、塌方就在眼前。据说也是百试不爽。
许多老矿工不敢把老鼠称耗子,都恭恭敬敬地称“爷”、“老爷”或“大爷”,不但在煤矿上不敢开罪老鼠,就是在家里也不敢灭鼠,怕得罪了老鼠井下遭报应。据说有位矿工家里来了位亲戚,带着只花猫,那只花猫果然厉害,果然好手段,一连几天几乎把那位矿工家的老鼠抓完了。又一次矿工下班回家正赶上花猫在捉一只老鼠,矿工连忙撵猫护住老鼠,没想到那只花猫身手矫健,一个“鹞子翻身”,咬住老鼠就跑。矿工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后来井下发生塌方,只死了一个人,就是他。当然这是传说,可煤矿井上井下的矿工都信,都信是真的。
其实,老鼠还有一项极其了不得的特异功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老鼠繁殖极快,最多可以达到“几十代同堂”。科学家把老鼠放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老鼠可以自由的繁殖,很快这个空间中的老鼠成几何增长,当它们增长到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时,老鼠竟然停止繁殖,母鼠停止受孕。如果还生存不下去,老鼠不会全部饿死,这时候它们就主动咬死一些年老、体弱、幼小的老鼠。老鼠真乃太聪明了,千百万年的生存考验锻炼了它们,也完善了它们的生存之道。老鼠有灵。
叁
都说广东人吃鼠,说得须眉毕见、信誓旦旦,但问了不少广东人,都说听说、好像、可能、也许、估计。但他虽是广东人,可确实不吃也没吃过老鼠。

老鼠肉香。亦有人为证,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教授、大学问家潘光旦。
潘先生吃过老鼠肉,不仅仅是他吃,他还招待当时在昆明联大的数位教授去家中享受此美味。
原来潘光旦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抗战以后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搬迁到云南昆明。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艰苦阶段,供应极差,三月肉不尝。有一天潘光旦先生下帖子请几位同事到家中小酌,开开胃。众人早就馋得口腔清苦,梦之最美无非就是一顿席,且潘光旦留美博士平时就非常讲究吃喝。众教授皆大喜,真可谓喜从天来。
在潘光旦家吃得极幸福,真有久旱得雨之觉,真有解民于倒悬之感,此言非吾言,俱清华之著名教授在潘光旦家边吃边喝时的感言。吃完收箸上茶潘先生才露底,说你们问我凭什么弄到的腊肉?是不是从美国寄来的?皆不是!他说咱们今天吃的是一顿鼠肉餐。说罢,领众人去厨房,果然,厨房灶上还吊着十数条腊好的大老鼠。众教授皆大惊,皆相视无言。
潘先生的小女说:“老鼠肉很好吃,又香又脆”。有位教授因为在潘先生家吃了老鼠肉,其夫人威胁要和他离婚,闹得教授后悔误吃老鼠肉悔得肠子老青了。从此素食,荤腥不沾。可见吃鼠之恶也,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和其夫人亦不能脱俗。
潘光旦有一番高论,不愧为中国的大学问家。他说老鼠的肉俱精瘦,无赘肉,高蛋白,肉类中的上佳之品也,且昆明的老鼠体壮个大,食之正好。老鼠偷吃粮食、啃咬衣物,且繁殖很快,生长不苛求外部条件,我们现在很多人吃不饱,没营养,没肉吃,为什么不吃老鼠?把老鼠送上餐桌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何乐不为?况且吃鼠只是人们的习惯问题,有人说鼠身上有疫,吃不好要吃出病来,其实河豚身上有剧毒,吃不好会吃出人命来,但现在不是依然拼死吃河豚吗?
肆
1958年到了,毛泽东发出号召,就是最高指示,消灭“四害”,“四害”之首就是老鼠。

那年连我们小学生都全心全意投入到消灭“四害”的群众运动中,我记得“送喜报”时,小推车上推着一车又一车的老鼠尸体,小推车四周都插满红旗。那时候“除四害”真是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捉老鼠连猫都不用,因为猫抓住老鼠叨到一边三口两口吞到肚里,让“除四害”的人拿不到成绩。记得每个工厂、单位、街道、学校、食堂、仓库凡是有可能有老鼠的地方都成立了“灭鼠专业队”,用鼠夹子、鼠笼子、下鼠药、掏鼠洞、灌水、堵白灰。后来看到一绝招,把一只活捉的老鼠的“屁眼”用细线缝住,然后放“生”。这只被缝住肛门的老鼠因不能排便,憋急了,就凶悍无比,它会咬死它遇到的一切老鼠,直到它最后憋死。这招不知是哪位高人发明的,申请没申请知识产权?
杀伤力最大的要数下毒药。据说当时用的毒药都是剧毒,用香油和拌料炒伴时,都有警察现场值勤,因为稍一不注意,人沾上一点立马翻眼。据说连部队的防化学兵、卫生兵都出动了,军民共同打一场灭鼠的人民战争。杀死的老鼠用担挑、筐抬、车拉,估计那年可能让老鼠陷入灭顶之灾。即使那样,灭鼠的战场也不可能打扫得那么彻底,于是第二年老鼠的天敌黄鼠狼、猫头鹰、蛇、狐狸、野猫,大量死亡。还是老鼠厉害,六十年代,老鼠繁殖得更快了,一窝一窝,一窝俱十几只,且都能茁壮成长,因为灭鼠运动已经过去了,而老鼠的天敌没有一个能像老鼠恢复得那么快,老鼠横行于城镇,遍布于乡下,终成燎原之势。
现在养猫的人确实多了,吃鼠的猫却越来越少了。

伍
刚到晋西北农村插队时,因为老鼠闹过“鬼”。
睡到半夜时分,仿佛被恶梦惊醒,但觉得脑门上似乎有窸窸窣窣的响动,又仿佛是忽忽喇喇的响声,又好像咕咚咕咚有小鬼在举着铁锤敲脑门,一下子惊出一身汗,咕噜一声从炕上爬起来,一个打挺站在炕上,细听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着屋外的枣树叶哗哗地响。赶快跳下炕,摸黑点着了油灯,小屋子是亮了,一片暗黄色的沉光,照到墙上、窗户纸上,灯苗一动一摇,四周墙上的投影一会儿变得狰狞可恶起来,一会儿变得像妖,像鬼起来,这些我们倒不害怕,我们嘴里念叨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耳朵却像兔爷似的张大了听,难道刚才真是做梦梦见鬼啦?什么事没有,虚惊一场,自个吓自个,又吹灭灯躺倒重睡。这回还没睡着就听见了,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就在脑门子上确实有动静,渐渐地由远而近,由小而大,由整齐到嘈杂,到乱麻似的。真有鬼啊,真像聊斋中讲的房梁上有吊死鬼啊,因为我听明白了,那声音来自头顶上。跳下炕点着灯,端着灯照房顶,一片白惨惨的回光返照,什么都没有,没照见鬼影。一夜闹了七八回。第二天才闹明白,是房上顶棚里的老鼠吃饱了喝足了再互相追逐着婚配呢,我问房东有多少老鼠在上面折腾,他说没准,多了会有十几只、少了也有七八只,那为什么不把它们聚而歼之?房东说:它们又不碍事,你又逮不住它,只好由它们闹去吧,这才叫咱过咱们的日子,它们过它们的家家。
说梁上君子,果然有生活。
有一次我跟着生产队长去库房出粮食,保管把库房门打开里面阴暗暗的,为防贼防盗库房的窗户都被用砖石砌死了,外面阳光灿烂里面黑咕隆咚。等眼睛适应后,我一眼看见蹲在粮食囤子上面,竟然齐刷刷的有七八只老鼠,老鼠们并不慌张,并不急着藏躲,反而鼓起贼亮贼亮的小老鼠眼,一动不动的在审视着我们。

我大惊,仓库里有耗子那还了得,疾呼队长有老鼠,队长不经意地说是有老鼠,我说那还不捉老鼠?队长不屑的说那东西比您都精,你能拿住?
事后,我问过保管,他说库房腾空时都要用白灰补老鼠洞,库房的地也是用砖砌的,砖缝都是用石灰灌封的,墙根是用石头砌的,窗户都是用砖石封的,谁知道那老鼠是怎么钻进去的?进了粮食囤的老鼠老天爷拿它都没办法,放猫进去不行,猫一进去就把粮食堆上打的印版全踩乱了,放毒饵就更不行了,这库的粮食都是人吃的,放夹子笼子更白瞎忙,粮食囤里的老鼠个个精,有的是粮食吃谁肯上套?老保管说,粮库里有句真理不怕鼠吃就怕人盗。
原来除了投鼠忌器外,还有投鼠忌粮。想起唐朝诗人曹邺的一首诗:“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请谴朝朝入君口。”
生产队饲养棚中,常常演出耗子和骡子争食的一出。
我们生产队有一头驾辕的老骡子,是我们生产队的功臣,饲养员每次喂料都要多加一把粮食。这形成了一条规矩,老骡子是单拴单住有一个食槽,免得别的牲口争食,但住在饲养棚中的老鼠却不守这个规矩,极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见了老鼠和骡子争食的场景。饲养员加了料刚一转身,不知从何处窜出五六只硕大的全灰色的大老鼠,大老鼠个个身手矫健,三尺多高的食槽顺着槽柱爬上食槽如履平地。为了抢食槽中的高粱,老鼠们就像蹲在船帮上的鱼鹰,一个猛子扎到水里衔上一条鱼又钻上来。这些老鼠好生了得,个个比着“手疾眼快”纷纷跳进食槽吃高粱,然后又一个跳跃跳到老骡子的鼻梁上耀武扬威。把老骡子折腾得只能摇头,急了就用蹄子踢地,老鼠一点都不害怕它,常常是老骡子仰起头,避开老鼠的进攻。等老鼠吃完它再进餐;有时候被老鼠欺负急了,老骡子就会剧烈的摇头,把颈下的铜铃铛摇得山响,这时候饲养员就会走过来,老鼠真贼,立时烟消云散,老骡子才开始安详地吃料。如果饲养员有事一转身那群老鼠立马像鬼魂一样又出现在食槽的帮上。
我来农村以前,在北京上见过老鼠,京片子叫耗子,但从没见过田鼠,到农村广阔天地才发现田鼠才是庄稼地的主人。

田鼠那年头多,几乎每畦每垄都有田鼠洞,早晨出工时远远地能看到田鼠们一群群,一家家,胖乎乎地挤在地沿上抬着前爪立直了身子正迎着朝霞在检阅我们这些上工去的学大寨大军。田鼠也极聪明,他们都牢牢掌握着安全系数,远远地他们决不理你,近到一定程度时,他们才呼的一下地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田鼠比家里的耗子长得喜人,胖乎乎的,圆滚滚的,脑袋也是圆溜溜的,嘴能咧得很大,不像家耗子似的尖嘴,嘴大吃四方。老百姓说,天底下饿死庄稼人饿不死田老鼠。
干活休息时,大家都往地头上一坐,抽烟闲聊没事干,但年轻人精力充沛坐不住,他们就带着我随便找个大田鼠洞,仔细看看洞口细土上的田鼠鼠爪印,判断此洞非死洞,有一大家子田鼠住在里面。然后就用铁锹在鼠洞的下边方方正正的直上直下的挖一个规规矩矩的立方体,挖一尺多深,告诉我明天来干活时,这个洞子下面至少有两只金黄色的大田鼠,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等到下半夜,夜深人静了,田鼠会觉得危险已经过去,地里确实没有人了,之后就会出洞散步散心,这时就会一脚踏空,掉到这个深洞中,想爬就再也爬不上去了。这时候它就会发出求救的呼唤,洞中的另一只大田鼠或公或母就会急急忙忙跑出来,结果也是一脚踏空,掉进去。我将信将疑,老鼠是鬼贼精,怎么会自己掉进陷阱?怎么会让另一只也掉下去寻死?
第二天上地干活我急急忙忙地跑到地头上一看,真神了!果不其然,立方体的土洞底下是两只抓耳挠腮的大田鼠,一见有人,吓得一个劲的往上蹿、往上爬、往上跳。但一切都是徒劳的。老乡告诉我,田鼠这东西最讲感情,如果一只公田鼠先掉进去,那只母田鼠明知是死也要心甘情愿的跳下去,一是为了救它,二是有难共赴,看着那两个惊慌失措的小东西我心里竟然产生出一些怜悯来。老乡们抓田鼠也不仅仅是为了玩,如果他们抓住一对白毛的田鼠,纯白的,像十二月的雪花那么白,拿到城里能卖三块钱,那岁月的三块钱顶住老乡一年的现金收入,老鼠再狡猾也斗不过人。
陆
明朝的宋濂写了一个老鼠斗不过人的小故事,说的有声有色的。说“鼠好夜窃粟,越人质粟于盎,恣鼠啮于不顾。”老鼠高兴之极,呼朋引伴,结队成行钻到盎中大快朵颐,不亦乐乎。过些日子越人悄悄的把盎中,即一种腰大口小的罐子中的粮食倒出来,灌进去水,然后再用一层糠皮漂浮在上面。“而鼠不知也。逮夜,复呼群次第入,咸溺死。”
老鼠再贼也贼不过人。它不知道三十六计中有一计,欲擒故纵。
原标题:鼠之杂记

白头翁作品《飘雪有韵远行无声》,此书分为3辑,一辑“雪落无声,风月有情”,是对既往人生岁月的追忆,有情有义;第二辑“历史无痕,花开有意”,是读书随笔,写的多是历史述评,对历朝帝王的点评,有声有色;第三辑“心灵无间,时空有序”,写的是心灵故事,充满生活情趣的小品随笔,有真有善。京东、当当均有售。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是购书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