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龙少年文学奖作品
厦门市松柏中学——李幸真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独饮。”
“瓢之漂水,奈何?”
“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
“水止珠沉,奈何?”
“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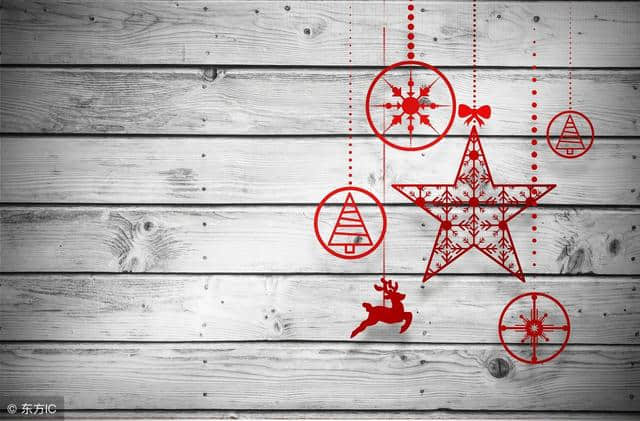
配图
年少结识诗书,只教“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硬着读罢。而后发现,实则不然,在与“红楼”相逢的时间里,我为宝黛二人的故事所感动,这段对话也烂熟于心。宝黛二人的结局似乎就在这段对话中隐约埋下伏笔,黛玉最终抱憾病逝,宝玉应着诺言出家。当年那句“禅心已作泥沾絮,莫向春风舞鹧鸪。”真真不是句玩笑话。既然你已离开,那我出家的心也就禅定了,任鹧鸪如何呼唤,我也不会想家了。没了你,我也便没了家。
自此,我对诗书产生了别样的情感,我不再为“颜如玉”“黄金屋”而读书。
佛曰:“照见五蕴皆空,能渡一切悲苦。”而世间多少痴男怨女尽在不言中,于诗间流传,他们的刻骨铭心穿越千年,跃然纸上,牵动我的情思。不曾想,我成为一个误入诗间的旅人,时而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望着雁过无痕,思念着远方;亦或是面对孤冢,与爱人阴阳相隔;再或者于茫茫沧海上,一叶扁舟,衣带渐宽,人儿憔悴;花开花落,岁月匆匆,世间只剩我一人,独自癫狂。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闻刀剑声声喑哑,鼓声镗镗作响。我将随孙子仲将军去江南,平定陈和宋。久经沙场,我本以为自己早已参透人情冷暖,将生死看淡。可人非木石,岂无感哉?遥忆那年对你起誓,无论死生,我都会牵着你的手,同你慢慢变老。可如今,我们之间竟隔了千山万水,我有多想见你一面,哪怕只是一眼?我明白,是我对不住你,离你太远,是我没有信守誓言,让这成了空话。《诗经·击鼓》哀婉苦楚,哪怕是铁骨铮铮的将士,心底也埋藏着深深柔情。爱上一个人,也便从此有了软肋。生死别离方觉人生苦短,天若有情,应怜铮铮剑寒。
人或许就是这样,穷尽一生苦苦去追寻那些已经逝去或者留不住的东西。死亡和离别尤其将这种情感放大得透彻了。很多时候,我们先感动了自己,而后才感动了别人。
东坡先生的作品,是古代文坛上的一抹靓丽的风景。他的作品有趣,而人也更为有趣。他的两袖清风,坦然自若,开朗豁达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中一览无余。他也可以为心爱之人而耿耿于怀多年。豪放疏狂,婉转悲凉在他的笔下转换自如。犹记苏轼的《江城子 记梦》,那种长达十年无法忘却的痛绞割着心,是《击鼓》也无法比拟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不知不觉过了十年,而你仿佛还在我的身边,你为何弃我而去,留我一人在这人间? 我对你的思念,一分一秒也未曾断过,这肝肠寸断的痛一直在心底蔓延。泪千行,我想有朝一日我们定会在天上重逢。
不思量,自难忘。但情难自己,总不能自说自话罢。
酒醒,河上烟波浩渺,暮霭沉沉,月亮被其掩映起来,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我回头张望,却不见那绿茵茵的杨柳,方信我已远离你。霎时,惆怅溢满胸腔,只得喃喃忧伤:“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的哀婉总是像水一般轻柔,将读者环绕。不论是这篇《雨霖铃》还是《凤栖梧》里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都能将我拉入他的世界,一寸相思万绪愁。
志与相思与愁,时常交织在一起,让人心底五味杂陈,却乐此不疲。
从欧阳修浅吟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到秦观低唱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有诗仙李白醉酒挥洒的“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更有铁汉辛弃疾奋笔疾书“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念着司马光的“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又想起了李商隐的“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情狂。”非我爱读这些风流佳话,只因文字的魅力总是越于礼法之外,并不强居于字句俨然。字里行间,溢满真挚,不加修饰地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成了他们故事之外的看客,他们与我皆是过客。彼此交错间,文字像一粒粒石子,砸向我的心海,一波再过一波。相思通常是无依无托的,而我却将其依托在了这诗书所展现的平行世界里,为那片刻感动而流连忘返。那感动教会我:忠一人,爱一生,行一事,致良知,勿忘从心之所向。
时过境迁,终不似,少年游。心渐渐沉淀下来,学会去理解,学会去感动。前些日春夏雨和软,催开百花新貌,也便信手拈来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几时起,那抹诗韵也揉进了我的骨子里,让我为之所动。
我不过是一个误入诗间的旅人,然相见即是缘,冥冥中我注定和他们相逢在今生的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