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的可怜与克厌—— 唐人矛盾的身体观
与魏晋时期士大夫们竞相追求“手持粉白, 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饰”的近乎病态身体审美不同,唐朝人在身体观念上崇尚力量与健美,就连文人亦将经常患病、体质欠佳视为可羞愧之事。如刘禹锡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就曾谈及自己这种心理,“愚少多病……及壮,见里中儿年齿比者, 必睨然武健可爱,羞己之不如”;王建也通过“健羡人家多力子,祈求道士有神符” 等诗 句表达自己对强健体魄的钦慕。寻常身体的弱质状态尚且能引起唐人如此多的忧思,其在面对残疾这种身体恒久的不完满时之态度就显得更为复杂而矛盾。反映了唐人这种纠结的情绪与态度。作为开放与包容之时代的盛世子民,唐人站在道德高点上对身体不健全者表现出了充分的同情与照顾,从制度上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伤残救恤体系。但当伤残之人真正来申请这些优抚时, 却会遇到许多困难与障碍。
例 4.1:
对折指判:甲缘木损折枝指,谓三疾数足。官不许事。甲禀气陶形,偶华胥之代;轻躯弱质,谢都卢之人。不能凿井耕田,翻乃奔林缘木。损其枝指, 盖是悬疣。虽折一枝,幸祛数外之累;即图三疾,便为非分之求。理不可依,宜从告免 。案件的主角甲体质孱弱,无力务农,只能以表演杂技爬杆谋求生计,然而在某次攀爬过程中发生意外,致使手指折断,遂向政府申请三疾救恤。 唐律规定“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瘇,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痴痖、侏儒、腰脊折、一肢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疾、癫狂、两肢废、 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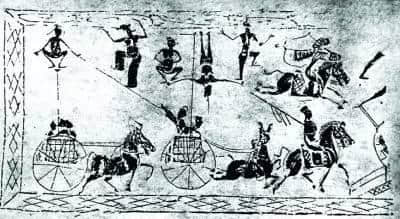
依此条文所 定标准,甲本可符合残疾之列。然而凑巧的是, 甲的手部先天畸形,生有六指,此次意外折断的正是这多出来的枝指。于是问题出现了:对甲而言,其确实因受伤而失去了手指;但在他人眼中,甲的身体状态却与常人无异。甲的伤残申请并未被通过,书判者的理由是,枝指本即为多余赘物,因故折去非但不能算作残疾,伤者反而应该为自己的身体回归到了正常状态而感到庆幸。但残疾与否的判定本应以伤残的严重程度及其给患者生活带来的影响程度来衡量,《唐律疏议》曾举“旧瞎一目为残疾,更瞎一目成笃疾,或先折一脚为废疾,更折一脚为笃疾”为例解说三疾之间的区别,就是以此为鉴定标准。 以甲的情况而言,判决时需考察的是枝指折损有否给甲原本之身体造成了创伤,及是否影响其赖以为生的缘木表演,而非看其断指后是否在外表上变得和大多数人相同。若甲之日常生活能力确实因此受到影响,则应考虑裁定为残疾。从原审 结果与判文内容不难窥见时人对身体异于常人者的排斥与不屑之态度,正是这种情绪与观点使得在现实中确切发生过的身体伤害在概念上被消解。这种对身体不健全者隐含的敌意与鄙夷不仅针对底层民众,即使出身世家贵族,躯体的羸弱、残障亦被视为可笑可鄙之事。残疾者更可能因此 而被除去承袭爵位家业、执掌祭祀典礼的权利。
例 4.2:
对嗣足不良判:景食一县,嗣子足不良,请立其弟,礼司不许。云:古有其道。 锡爵启土,将以畴庸;开国承家,寄于令嗣。乙受封一邑,参荣五等,高门不昌,厥子婴疾。 昔郤克为使,取笑齐人;孟絷不侯,称于鲁史。况主丧祭之礼,如有朝觐之仪。继代非轻,择贤而立。有符故事,无爽通途 。庆食邑,象贤继踵。承家之道,将不愧于前修;畴嗣之宜,庶遥符于古义。眷言长嫡,疾乃天然。既类郤克之刑,将同孟絷之废。且仲子立衍,循鲁礼而知归;韦家封成,镜班书而有序。瞻惟乙请,未爽通规,在律虽违,行权则可。请停司禁,无拒乙辞。大夫称家,荣高食采;冢子当室,业茂本枝。盈大足徵,期克昌于魏国;六三能履,或取笑于齐堂。弱足者居,奉身而退。遵康叔之命,以崇 次及;察韩黯之衷,雅符高让。则先茅旧土,今也载传;孤竹遗风,此焉无替。法听弃疾,礼贵象贤。立弟舍兄,理复何惑? 景有食邑一县的爵位,因其法定嗣子不良于行,而上请另立继承人,然而负责管理爵位更替的礼部未予批准,景又以古时即有先例为由再次提出申诉。唐律封爵令规定“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习,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 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 玄以下准此。无后者国除” 。
对照案情叙述与律令条文,可以得出几点信息:其一,景之嫡长子自身尚无子嗣,否则按律嫡孙在袭爵顺位方面优先于嫡次子;其二,嗣子的足疾应该并不严重,若实属重患,景可直接凭律法“有罪疾,立嫡孙; 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之令文提出变更继承人的申请,无须拐弯抹角的攀援前代故事。此案有趣之处在于,其本身非常类似太宗家事。唐太宗即位之初即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而李承乾长大后恰巧就是足不良,当时群臣中就不乏以此为由奏请更换储君者,“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上表言: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上曰:我识卿意,我儿虽患脚,犹是长嫡,岂可舍嫡立庶乎”,尽管太宗明确表示不欲因太子足有微恙而废嫡立庶,李承乾却自卑忧虑,“恐 有废立” ,以致终行悖逆之举。李安俨的意见正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身有障碍者的态度。这种唐初就有所表达的对肢体不健 全者的排斥,在此案的判文中愈发凸显出来。在给太宗的上书中,因当事人乃帝王爱子、一国储君,谏言者尚不敢过分表露其轻嫌之态。而此案 件所涉之嗣子,既然连其父都已将之放弃,书判者就更无所避忌,判文中不屑之情表露无遗。三篇判文皆引用春秋时晋国的郤克出使齐国时因不良于行而遭到嘲笑之旧典,作为支持景更立嗣子的理由,并提出肢体不健全者就该主动退位让贤, 以免贻笑大方,最后三人一致判定景申诉合理,足疾在身的嗣子应被更换。
然而书判者在引郤献子之典故时有意无意的遗忘了一个事实,即郤克在晋国其实深得景公重用,兼任执政大夫与中军元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平衡诸卿,对外积极用兵,最终大败齐国、戎狄,其文治武功使晋国的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 郤克既未因跛足失去家业的继承权,亦未因此而见弃于国君,反而取得了诸多成就,他恰恰是不 应以“身”取人的明证而非反例。唐代官僚士子们对身体不健全者的敌意与鄙 夷充溢于判文的字里行间,齐顷公母子对郤克无 知又无礼的嘲笑在其笔下被合法化,仿佛残疾人受到讥讽是理所当然。寻常立嗣时所争议的嫡庶之分、长幼之别、贤愚之辨,在不完美的身体面前都失去了声音,没有书判者考虑过景原本的嗣子是否身残志坚、才能卓越,仅凭跛行可笑一条 就否定了其承袭祖业的权利。且有两篇判文都称景欲改立身体健全的次子为嗣是“择贤”“象贤”,言外之意即身患足疾的嫡长子“不贤”。原本对身体的认知被莫名的嫁接到道德领域,似乎某人在肢体上的不健全同时意味着其品行、才能的缺 失。法国人类学家大卫·勒布雷东在分析西方社会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时略带批判的指出,“‘残疾’承受着社会的谴责,活在有关人的负面评价详细法则之中” ,此论断大抵同样适用于唐代的中国。
日趋仪式化的卫生保健制度
自远古起,国人就在有意无意地积累有关维护健康和预防疾病之知识与方法。进入王朝时代后,许多行之有效的卫生保 健措施被从国家制度层面确定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如“藏冰”“伏日”等,这些制度传至唐代,其性质与初设之时相比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例 5.1:
对春不修鉴判:丁掌冰,不颁于命士, 春不修鉴,而辄秋刷。开国承家,建官分职,品彚斯布,卑高已陈。故礼设六官,必在所掌;司分九命,且均其职。 眷彼凌人,颇忝班位,惟兹命士,实厕周行。虽和平在时,终无天昏之理;而炎凉失节,或生疾疫之事。备预之道,宁失国经?颁赐之仪,岂乖常礼。且湥溪寂寂,方委积于大冬;虚室寥寥,遂收藏于小吏。春风已解,不闻修饰之功;秋露未圆,方事刷清之业。当其时而不作,已表非勤; 应合给而缺供,尢彰失守。不应之罚,从此自贻; 慢令之科,宜以为始 。宗周布政,汉家旧法。藏冰于陆,自古有之; 颁冰于朝,方今靡替。倚那厥职,乃丁是掌。西攀咸镐,寄甘泉之北宫;东邑巩洛,入邙山之阴洞。 履霜知坚,和翠微而一色;积雪偕冻,岌稜层而 流寒。当忝司存,合闲主守,苟违命士,得无常刑。 若惟陈迹,良亦异闻。且太岁换韶,盛德在木。 上从天子,下际群公。大给千官,备霑累命。青荧片片,光研金镜之空;瓶峨峨,姿凛玉壶之态。 盖将以荡清暑,辟炎毒。水晶帘内,飞燕娇歌而对山;虎魄盘中,省署永吟而陶酒。时或稽缓, 人必其忧。况士不颁冰,阙也;春不修鉴,怠也; 秋仍辄刷,非也。三者备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 请用常典 。 据《夏小正》记载,夏朝已设有专司用冰事宜的“颁冰人”之职。周代置“凌人”掌管藏冰、 用冰之事,今之考古勘探已发掘出战国时期的藏冰建筑“凌阴”遗址。《左传》中记载当时之藏冰情况为“其藏冰也,深山穷谷,涸阴沍寒,于是乎取之” 。藏冰之举在后世多有延续, 唐代亦继承了这一制度,并设有专司藏冰之部门。 然而在此事件中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唐代藏冰的使用范围和日常管理办法同古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传》所载的颁冰对象为 “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以达到“冬无衍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疠疾不降,民不夭札”的目的。

现存皇家冰窖
若据此段文字所述,其时受冰之人范围极广,从贵族至百姓普遍都可获得冰的使用权。而至唐代,如案情所述,藏冰基本只颁给身为达官贵族的“命士”,有时即使连命士也难分到冰。从《全唐文》中所收载的诸臣答 谢君王赏赐之表文看,当时作为赏赐的主要物品 多为金银器物、口脂面药、饮食衣饰等等,而很少以藏冰予人。而白居易所留《谢赐冰状》一文, 更证明了当时的藏冰是需要有帝王特别授意方可 领受的特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有案中“丁掌冰,不颁于命士”的情况出现,唐代规 定每年藏冰总数一千段,供应大小各种祭典场合及皇室私用恐怕已经不甚宽裕,根本无力再实现古时“其用之也遍”的防疫理想。第二,从案情叙述“春不修鉴,而辄秋刷”一句及两位拟判者所论述的内容,唐人对古书所载之藏冰在理解上似乎出现了某些偏差。此句诉讼的来由应为《周礼》“凌人掌冰政……春始治鑑,夏颁冰,秋刷”之文,据库狄履温和廉粲 判文之意,显然是将“治鑑”理解成了修葺打扫藏冰之地,认为丁掌冰应该在春天整理清洁冰室, 而非到了秋天才开始扫洒。“春风已解,不闻修饰之功;秋露未圆,方事刷清之业。当其时而不作,已表非勤”“春不修鉴,怠也;秋仍辄刷,非也。” 但此种观点恐怕是对古礼之误读,春季时气候回暖,而冰室中正储存有大量未启用的冰段,若此时开启冰室,大肆整修建筑、打扫清洁,必然导致藏冰不固、冰块融化。秋季气候肃爽,且处于旧年库存之冰已经尽数颁出,当岁将藏之冰尚未开采之际,正应利用此段空闲时间对冰室加以洗刷打扫。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解释“秋刷”句云“凌,冰室也;刷,清也;刷除凌室,更纳新冰”。可见丁掌冰秋季清刷冰室正是合情合理,反而是两位书判者理解有误。导致两位误判的正是古文“春始治鑑”一句。《周礼》所言之“鑑”并非用来 藏冰的冰室建筑,而是春末启冰之后用来作为盛冰容器的冰鉴,郑玄释“鑑”为“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春而始治之,为二月将献羔而启冰。”这种冰鉴一般由 木材或青铜器制作,将冰块放入其中后既能用来冷藏食品,又可使其直接散发冷气,起到降温的效果。若将“春始治鑑”理解为初春就先将可能用到的盛冰容器治办修整完备,则从文辞大意及实际运用的角度都解释得通。虽然书判者的文中也提及藏冰是为防疫,但从二者皆不甚了解冰凌的实际保存与运用情况看,他们可能只是习惯性的引经据典,实际上并未亲自参与或目睹过藏冰、颁冰等活动。佐以其他与藏冰相关的案例可以推知,这项在古代卫生保健措施,流传到唐代很可能已经形式大于内容。除了国家祭典和高官丧礼等场合,普通官员日常很难获得国家颁冰,更毋论与民防疫,用冰已经成为仪式的环节和身份的象征。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伏日制度。

皇家冰窖——冰块开采
例 5.2:
对伏日出何典宪判:广汉等四郡,俗 并不以庚日为伏。或问其故,云:地气温暑,草 木早生,异于中土,常自择伏日。既乖恒经,出 何典宪? 广汉之郡,实惟沃壤。江波濯锦,斜分白马之津;山嶂吐云,近对黄牛之峡。皇明抚运,文 轨大同,自北徂南,东被西渐。徒以窪盈异等,风候殊宜,草木偏早于阳春,金火不取于令日。炎蒸郁毓,未见行车;毒雾氛氲,唯看坠鸟。论其恒式,违帝者之金科;语以宪章,符汉王之故事。是非之理,其在兹乎 ? 天平四序,有寒暑之殊;地列九州,著华夷之别。风土既其不等,节候于是莫同。广汉夷陬, 境连巴俗。岷隅沓转,云峰与霞岫争辉;江溜横分,锦派共沙湍递映。候乖中壤,叶茂三秋;气离炎州,草长二月。至若时锺季夏,节一重阳,金方始萌,火德不竞。非无典司之主,必告伏匿之辰。当复取舍因循,何得辄为改革?国家明堂布政,象法已行,岂使均雨之乡,翻闻易日之义?虽殊风俗 之典,恐非得时之宜。勒依恒式,谓符通理。斗建于戌,知立冬之景星;火胜于金,故至 庚而气伏。徵历忌之故事,因禀阴阳;按方志之所宜,或殊寒暑。广汉四郡,蜀门九折,通濯锦之流,入青衣之徼。徒以温暑异于中夏,畜驭同于夷狄,许令自择伏日,所以遂其土风。当令齐七政之明,垂四方之则,百蛮由其奉朔,九译于是同文。况兹巴蜀之人,素陶齐鲁之教,自当变而至道。率乃旧仪,苟乱人时,奚同文轨?风俗通之小说,未足宪章;中和乐之雅音,须崇舞咏。清下四郡,俾依三伏 。 伏日之设始于春秋时的秦国,至汉代已成为常规性的仪典。其设置之初出于卫生保健的考虑: 自初伏之日起,即进入一年中气候最炎热的时节, 民众应自此日始伏匿不出,以躲避盛暑,预防疾 患。
汉代有“初令伏闭尽日”“伏闭门”之习俗,魏晋诗人程晓的诗作“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 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 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伏日蛰居避暑的情境。而在入伏之际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典,以祈求甘霖清爽、避暑消灾。 既然涉及祭祀及休假,对伏日时段的择定就成为一件较为重要的事宜。汉代起即习惯将干支庚日与节气相结合确定入伏之日,一般从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算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始入中伏, 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进入末伏,入末伏十日而出, 当年之伏日结束。 唐代在伏日的设定上基本沿袭了汉制,但其时中国之疆土幅员辽阔,南北气候情况差异巨大。南方之节令实际远较中原为早,酷暑降临也要提前得多,所以许多州郡都不遵国之常典,而是根据本土实际气候情况自行选择伏日时段。此案之争即由此而起。同样的问题在汉代显然也存在,而当时之处理方式如东汉应劭所撰《风俗通义》记载,“汉《户律》云‘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曰: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即允许南方各地依据气候环境自行选择伏日时段。此举本是符合实际之策,但到唐时却出现了争议。
从判文可见三位书判者的态度,除崔翘不甚明确地传达出或许应该允准广汉四郡自行选择伏日之倾向性,其余两人都表示尽管南方风土确与中原不同,但国家典章制度不容轻易更改,四郡理应遵守国之恒令,邵润之甚至认为《风俗通义》乃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其所谓之“汉律”亦不足取信。今存唐代文献中既未见允许地方自行选择伏日之记载,该案之结果大概可以推知。此种处理其实有违设立伏日以教民避暑防疫之初衷,而将其变成了徒具形式和象征意味的节庆祭典。综合此类判文可以发现,许多古时颇有实践意义的卫生防疫制度发展至唐代,其实质性的内容渐行弱化,最初的医学内涵逐步流失,而演变成带有某种隐喻意味的仪式,形式合礼性渐渐优先于实际有效性。
寻找疾病的负责人
有些时候疾病的发生可能受到身体状态不佳、外部环境恶劣、劳逸作息失当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并非某个人有意或无意的过失所致。但 在唐代,人们似乎希望给疾病的发生找到一个恰切的责任承担者,第六类判文正反应了唐人的这种心态。
例 6.1:
对庐树判:商子行,饮食失节,生疾。 抑云:庐氏井树不修。先王作则以广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树,旅有施舍;相彼庐氏,实曰职司。在故事之允修, 于从政乎何有?既而日暮途远,商子载驰,辕端莫向,马首靡托。既伤行旅之感,加之暴露之忧。寒温失时,以干六物;饮食不节,是生百病。且国生纳币,咎在晋卿;江氏失布,盗由楚相;玉毁于椟,罪有所在 。 四人有业,天下同归。理在营生,方光润屋。货贿山积,是往来于五都;珍奇海输,乃森罗于九市。睠言商子,实职贸迁。袭弦高之风,为绛候之事。经途所亘,多跋涉之劳;饮宿乖宜,爽阴阳之候。野庐所掌,井树是修。何得旷于主司,致有损于行李?遂使银床罢汲,无郝子之投钱;碧树摧荣,闻茅生之危坐。盍归司败,以正刑书。惩其已犯之愆,永息将来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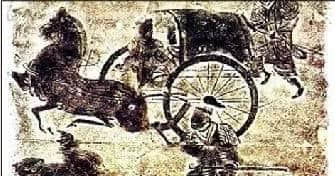
此案是某商人在行旅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 身体劳倦,饮食又无规律,以致罹患疾病。这本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商人认为自己之所以患病,与掌管交通庐舍之官吏未将宿息之所修缮妥帖脱不了干系,于是有此案之诉讼。以今日之眼光看来,这一诉讼似乎不甚合理,即使管理者未将庐舍营葺完备,使其住宿期间休息得不够舒适,亦非其生病的直接、主要因素,不至于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但从判文内容来看,两名书判者显然都认同庐舍之管理者应对商人患病一事负责。在明知该商人生病的主要原因是饮食失节的情况下,仍科庐氏“井树不修”之罪,似乎有将失职之过与致病之罪相混淆的嫌疑,也从侧面体现出唐人希望有确定的“某个人”能为疾病的发生负责的心态。
例 6.2:
对漆室染疮绯衣版授判:甲逢故人,引入漆室,遂患漆疮,诉云料理。又景版授刺史, 著绯袍,村正云不合。甲以芝兰同味,早托葵歌;景以蒲柳侵年,方忻艾寿。烟火相接,昔是往来;雷雨或覃,即承恩造。鹑居鹜饮,共申东户之游;鹤发鸡皮,载煦西山之景。既无猜于杵臼,遂有奉于丝纶。携手入门,引故人于漆室;披襟就服,僭常例于 绯衣。乙如聂政之容,相看不识;景方庞统之秩, 即事何惭?头面有疮,自均无过;耳目不审,岂假论辜。拊其诉端,堪取笑于周客;详其告状,欲何罪于尧封?染患自是晦明,在法宁加老耄。探情未亏于通恕,据律不犯于正条。便寘严霜,虑伤非罪,乙与村正,咸释为宜。
该判文为两案合拟文,其中第一案即与医事相关者。结合判文内容看,甲应是漆工,路遇故友乙,遂将其带入平日制作漆器之房间叙旧,不料乙对漆过敏,头面部遍起漆疮,因此与甲对簿公堂。此案若发生于汉魏六朝时期,是非如何或许仍存争议。然而随着隋朝病源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的问世,人们对漆疮一病有了新的认识。《诸病源候论》“漆疮候”有言“人无问男女大小, 有禀性不耐漆者,见漆及新漆器,便着漆毒,令头面身体肿起,隐胗色赤,发疮痒痛是也" 、“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这段论述明确指出是否感染漆疮实则取决于个人体质。正因有此医理作为基础,书判者认为乙染患漆疮之责任主要仍在其自身,甲之举动既然并非蓄谋,是以不应加罪。此案不仅反映出唐人为疾病寻找责任人的心态,而且充分展现了医学认识发展进步的社会意义,“漆过敏与个人体质相关”的认识使疾病责任的划分更为明晰,从而避免了 误判。
现实医疗与典章律令的矛盾冲突
唐朝律令受中国自古文明形式之影响及时代条件制约,多有不同于今日之特殊规定。而受限于当时的医学总体治疗能力与职业医人的数量,唐人遇到某些疑难病证时,往往会寻求正统医学之外的治疗方法或养护措施。有时这些民间救疗手段很可能会与部分律法规条相碰撞。又有些时候,律法赋予病者某种程度上的特权,但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则却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贯彻执行。第七类判文反映的就是患者在养病疗疾时的某些过程、方法同当时之法律、道德发生碰撞的各种情况。
例 7.1:
对父病杀牛判:壬父病,杀牛祈祷。 县以行孝不之罪,州科违法。 力施南亩,屠则干刑;祭比东邻,理难逢福。冠带纵勤于侍疾,鋩刃宁同于彼袄。壬忧或满容, 杀非无故;爱人以德,未闻易箦之言;获罪于天,遂抵椎肥之禁。志虽行孝,舍则乱常,父病诚切 于肺肝,私祷岂侔于茧栗。且宋人皆用,或免乘城之虞;魏郡不诛,终非弃市之律。令不惟反,政是以常,县恐漏鱼,州符佩犊 。乡人壬的父亲患病,或出于医药不效等缘由,选择通过杀牛献祭、祷告祈福的方式,来治疗父亲的疾病。但杀牛在唐代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县衙长官体谅其举动出于孝心,未加苛责,然而州府之管理者从行为结果论,仍判其违法。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面对广袤的耕地与繁重的农务,人自身之生产力是有限的,牛作为辅助人类完成田作的主要畜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价值,许多朝代都有严禁屠牛的法令。唐律明确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 一年半” 。壬之行为无疑是典型的“故杀官私马牛”罪,之所以有此案之争议,是缘自其行动过程始终伴随孝亲之目的。在讲求“百善孝为先” 之古代社会,符合最高道德标准之行为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法外豁免权的。如《旧唐书·李勉传》载“部人有父病,以蛊道为木偶人,署勉名位,瘗于其陇,或以告。曰:‘为父攘灾,亦可矜也’舍之”{,同样是为疗父疾而触犯律法,甚至此
例中的“部人”严重冒触了长官,但却因孝心可悯而被释放。另外,“杀牛祷病”也与当时某些特殊的民间风俗有关,据《朝野佥载》所载,“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此一社会背景也带有些削弱责任之作用。基于以上两条原因,才有县级审判时的宽大处理。然则最终复核此案的元稹认为,尽管壬行孝之志可悯,但屠杀为人出力之耕牛,不仅触犯刑律,而且有伤天德,以此祈祷实难蒙被福泽。同时元稹点出了此案的另一关键情节,即只有国之祭典才能以牛为牺牲,壬小民私祷,竟亦屠牛祝祷,实过于僭越逾制,此点若是深究恐怕罪责更重。不能因壬为行孝之隐衷就打乱国之常法,且州府既已做出判决,令出当行,不宜反复更改,是以仍须治其杀牛之罪。而从此案的案情与判文中除了可以了解到当时某些民间疗法与律法规范的冲突外,也可以看出当时南方与北方之间、普遍民众与知识阶层之间对于疾病和治疗的不同认识观念。
例 7.2:
得甲在狱病久,请将妻入侍。法曹不许。诉称:三品以上散官。 狱虽慎守,病则哀矜;苟或无瘳,如何罔诏。甲罪抵刑宪,身从幽絷。忧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 危则思亲,缧絏之中有请。势穷摇尾,念切齐眉。 卧或十旬,既轸弥留之惧;官惟三品,宜从侍执之辞。敢请法曹,式遵令典。与前例恰好相反,此案是唐律赋予患者的疗疾养病之权利在现实中最初未能得到保障。这里 涉及唐代一条特殊的法令,即狱囚病重可得家人 入内侍疾。 案情本身非常简单,囚犯甲在监狱中染疾已 有多时,于是申请让其妻来牢房照顾病体,但未能得到司法官员的允准,甲乃上诉称自己原为三品以上的散官。唐代刑法规定对在狱囚徒“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参照此条规定,甲即使只是普通囚徒,在其卧病已久的情况下,
申请让妻子独自进囹圄侍疾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应该获得批准,何况其还曾任三品官,按律更可得到两名家人入狱看护的待遇。甲之申诉提出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书判者亦未加为难。白居易的判文言简意赅地指出甲情堪哀悯、理循典章,有司宜准其申请,许家人入侍。实则依唐律所规,在此情况下主司不允许甲之妻到狱中侍疾反而是违法的,“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杻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按此条文,原则上来说甲有权利追究法曹“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之责。唐代律令对狱囚可能涉及的患病、医疗与养疾等相关问题已考量的较为周全,对重病患者不仅提供医药救助,而且允许家人入内照看护理。但通过此案也不难窥见,在制度与现实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落差的。
8. 其他涉医疾案例
除了可以归入上述七种主要类型的判例外, 还有零星数则与医药、疾病相关,但较难加划分的涉医判文。它们从公务期间卜居养疾的问题、体弱多病申请提前致仕的问题、因病耽误官职铨选的问题等方面, 反映出唐代与医疗、疾病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
综上,判文作为唐代重要的公务文书,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各种社会冲突、矛盾的司法裁决结果。而其中的涉医判文,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与医事相关的诸多争端与问题以及书写者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对《全唐文》中所收载唐人判文的梳理,主要体现为七类:第一类与唐代药材流通中存在的产地不清、作伪、哄抬药价等问题相关;第二类展现了当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不同阶层的医疗需求差异对冲突处理结果的影响;第三类有关当时较为常见的诈病现象,判决结果往往取决于称疾者之目的;第四类透露出唐人对不健全之身体既同情又鄙薄的复杂情绪与态度;第五类涉及古代卫生保健制度的流传至唐代日趋形式化的演变趋势;第六类反映了唐人希望为疾病的发生寻找责任人之心态;第七类则是病人治疗过程与当时之法律、道德间出现矛盾碰撞的各种情况。这些判文多角度展现了唐代社会医事活动的不同侧面,生动、细致地勾画唐代医疗实践的整体面貌。从中可以略窥唐人对于疾病、治疗等问题的观念看法以及当时医生、患者的现实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