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研究中,曹学是一个重要的分支。贾府的故事隐含着曹家的事实,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十个《红楼梦》的读者有九个会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殊不知这个回答并不完全正确。
随着《红楼梦》小说和电视剧的走热,有的观众不免会心生疑问:贾宝玉的原型真的是曹雪芹吗?书中的贾家即是现实中的曹家?曹雪芹写此巨著的灵感从何而来?
其实,破解《红楼梦》的诸多谜题,需要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开始。那就是首先要搞清楚《红楼梦》故事的创作者是谁?
曹家的败落是在雍正六年(1729)。据学者考证,彼时曹雪芹至多不过十三岁,织造府的繁华留给他的印象应当是有限的,在这个年龄上谈情说爱似乎也为时过早。因此,大观园中那位翩翩公子,至少不是曹雪芹个人的写照。
实际上,《红楼梦》故事的创作者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曹雪芹,而是另有其人!!

曹雪芹
红学家们注意到:熟悉《红楼梦》创作情况的脂砚斋,曾在脂本批语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他本人就是宝玉的模特。
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也曾写道:“闻其(指曹雪芹—引者)所谓宝玉者,尚系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裕瑞的“前辈姻戚”曾与雪芹交好,他的话当非空穴来风。此外,据裕瑞转述,曹雪芹生得“身胖头广而色黑”,这虽是雪芹中年时的形象,想必其年少时也不会怎样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裕瑞还说:“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听其言而想见其为人,也并不像冷然要去出家的神态。
总而言之,《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曹雪芹,二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红楼梦》研究的视点:是局限于一家一姓的史料钩稽、继续深入考索呢,还是把眼光放开,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进行探索和思考?本文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并有意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性探讨。
以往,有人从贾宝玉的脾气秉性、言谈举止去反推曹雪芹的为人,以为对曹雪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然而一旦切断宝玉与曹雪芹的必然联系,人们就会发现,对曹雪芹的情况实际上知之甚少。
曹雪芹究竟是曹家那一房子孙?他的确切生卒年月如何?他一生经历又是怎样?他的思想性格真的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模一样吗?几乎一切有关曹雪芹的话头都得用问号作结。
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曹雪芹生于富贵之家,青少年时遭逢变故;还知道他富于文学才华,喜作诗又好喝酒,颇有点名士派头;晚年则贫困益甚,埋头著书于北京西山;不上五十贫病而卒。仅此而已。对于一代大文豪,这些间接得来的零星材料,真是少得不成比例。
拿这点材料去跟贾宝玉对号,也只有出身经历这一点约略近之。然而,脂砚斋的出身经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广而言之,古往今来翻过筋斗的又何止曹家子弟,谁又能保证,宝玉形象中就没有他们中某些人的影子?
不错,曹雪芹初作《红楼梦》时,恐怕未尝没有为曹氏家族立传的念头。《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情节,也确实是从曹家的真人真事为依据的。然而小说创作自有它的规律,思路一旦打开,笔便容不得真实材料的约束。一时之间,作者个人的经历,家族的故实,朋辈的笑谈,前人的文章,乃至小说戏曲、街谈巷议,旧梦新闻、臆想虚构,一齐奔来腕底,一任作者採撷拣选,输入他的故事。彼时的作者,真如老僧入定,走火入魔,哪里还有那份冷静去考订“史料”、分辨虚实?这就是文学创作特有的规律,也是诗人有别于史祝的重要之点。明乎此,我们再来探讨贾宝玉的原型,便不会再受“自传说”的束缚和羁绊了。
事实上,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男主人公,他的形象很难摆脱作者的影子。至于脂砚斋以贾宝玉自居,他的话也并非信口开河。然而宝玉所受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这两个人。古往今来的逆子叛臣、高人奇士、纨绔子弟、多情少年,都有可能对宝玉形象产生过影响。在这些人中间,我以为有一位明末遗民对曹雪芹塑造宝玉乃至创作《红楼梦》影响颇大。但是他的启迪之功,至今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此人就是明末著名的小品圣手兼史学家--张岱。

张岱
张岱,约卒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他死后大约三十五年(此处依然以雪芹抄家时十三岁推算),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中呱呱坠地。对于雪芹来说,张岱是个近代人。他于明亡以后隐居越中,著书自娱。他生前就颇有文名,且有十几种文集行世。
拿宝玉故事跟张岱生平相对照,人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宝玉与曹雪芹的为多。
张岱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至少活了八十四岁。张岱生于一个累世通显的仕宦之家。他的高祖天复、曾祖元忭、祖父汝霖三代都是进士;元忭还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父亲张耀芳在仕进之路上却不顺利,然于五十三岁时,以副榜贡谒选,授鲁潘右长史,仍不失禄位。
生长在这个阀阅世家的张岱,对出仕做官却没有多大兴趣。他“少工帖括”,然而“不欲以诸生名”(《陶庵梦忆》雁云甲编本序)。靠着父祖的余荫,他在有明一代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一切传统士大夫文化所能提供的物质的、精神的享乐,他都尽情地受用过了,并深得其中三昧。这种豪华的纨绔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将近五十个春秋。
可是甲申年那场改朝换代的陵谷之变,彻底改变了张岱的命运。国破家亡的惨祸,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了他双重打击。他于“无所归止”之际,毅然“披发入山”,过起了“駥駥为野人”(《梦忆自序》)的隐居生活。一个在富贵之乡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一旦跌入“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同上)的贫困境地,他的感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在《梦忆自序》中,他把两种形同霄壤的生活境遇做了近乎戏剧性的对比。他说: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稀,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塏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面对冷酷的生活现实,张岱只有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然而佛门的因果报应之说,并不能抚平他内心深处的创伤。每到睡梦中,深埋心底的家国之痛,就以重现旧日生活场景的形式浮上心头。张岱在《西湖梦寻序》中说:
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而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
对张岱来说,西湖这个昔日的优游流连之所,实际已变作一个符号,成了故国山河和旧日岁月的象征。张岱每天做梦,也每天写梦。做梦和写梦成了他后半生唯一的生活需要和乐趣。大概只有沉溺在对旧日繁华的追忆中,他的心才能得到片刻的平静和温暖吧。他“著书十余种,率以梦名”(《绍兴府志·张岱传》)。《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都是著名的记“梦”之书。到了晚年,他索性更其号为蝶庵;这位心灵沉浸在昔日梦幻中的老人,此时大概真的分不清“蝴蝶梦我”还是“我梦蝴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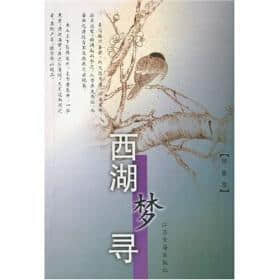
总结张岱的一生,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张岱生长于阀阅世家,环境既富且贵,弥漫着文学气氛;
(二)张岱的功名之心十分淡泊,他一生都没有做官;
(三)张岱中年遭逢世变,物质生活一落千丈,内心世界苦闷万分;
(四)张岱晚年笃信佛教,希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求得心灵的解脱;
(五)张岱后半生写了大量忆旧文章,所结文集喜以“梦”字命名。
我们不难看出,张岱生平的简要总结,几乎就是宝玉故事的写作大纲。这是出于巧合,还是别有原因?
有关张岱身世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张岱《自为墓志铭》和《陶庵梦忆》序中。这两篇文章以其独特的“忏悔录”形式及诙谐自嘲的风格,迥然不同于一般的自述性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张岱之前,还没有什么人乐于把“吾之癖错”写进自传,以期传之后世;张岱偏偏开了这个头。而曹雪芹恰恰把这样一种风格贯穿于《红楼梦》中,这不能不说是雪芹借鉴于张岱的一个佐证。
总而言之,在研究曹雪芹与张岱的关系时,有一点是应当特别指出的:在《红楼梦》问世之前半个多世纪,一个自暴其“丑”的过来人故事,已由张岱展示给世人。数十年后,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脚下酝酿着《红楼梦》的写作时,他至少不是头一个触摸此类题材的文学家了。我们尚未掌握切实的材料,可以证明曹雪芹一定从张岱那里获得启示。但应当强调,曹雪芹是完全有条件读到张岱著作的。而且如果读过,作为有着类似生活体验的人,他一定会受到比别人更强烈的感染和震撼。
此外,张岱写过《家传》、《家传附传》及《五异人传》,叙述他的父祖及兄弟辈事迹,那些文章就收在他的《琅嬛文集》里。不知是不是这些文章启发了曹雪芹,使之产生写一部“家传”的初衷?当然,前提仍是雪芹必须读过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