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刘以鬯百岁诞辰。而刚刚半年以前,2018年6月8日,“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刘以鬯离世。刘以鬯是香港文学史绕不开的一位作家,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派的重要人物,但即便在去世时掀起讨论,他的文学价值依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对刘以鬯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遗憾。
为了重新发掘刘以鬯作品的文学价值,让他的优秀作品被更多读者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6月份出版了“刘以鬯经典”系列。这套书包括刘以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典作品:长篇小说《酒徒》,长短篇小说合集《对倒》,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寺内》。201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接着推出了刘以鬯小说散文合集《我与我的对话》。

刘以鬯
作为香港乃至中国文学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刘以鬯的小说虽不宏大,其名字却必将留在文学史中。在现代性写作迟滞的中国,他的探索如同一股清流,开拓出了自己的风格。12月5日,在刘以鬯百岁冥诞来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邀请著名学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老师,由“刘以鬯经典”系列责编陈彦瑾主持,与读者在线分享了他对刘以鬯先生的解读。许子东认为:“如果我们要从香港文学找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金庸,一个是刘以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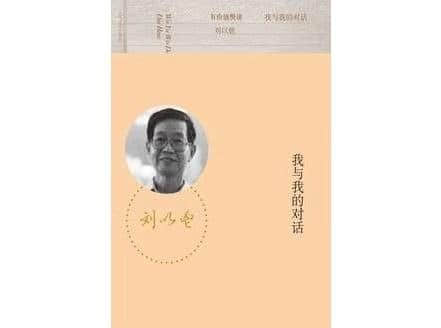
《我与我的对话》,作者:刘以鬯,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
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来到了香港
陈彦瑾:您和刘以鬯先生都是上海人,有报道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用上海话交谈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许子东:那个时候三联书店要我编一套《香港短篇小说选》(香港的严肃的纯文学的小说选,每两年出一本),我接手后就去拜访几位重要作家,刘以鬯、西西,还有其他一些人。当时刘以鬯是《香港文学》的主编,我就到他的编辑部去。我们见面感觉很亲切、很温暖。他平常没有太多机会讲上海话,我在香港也没有机会讲上海话,所以我们用上海话讲了好几个小时。他讲他原来在上海怎么开始喜欢文学,跟姚雪垠他们的来往,到香港以后怎么辛苦,又去南洋编报纸,总而言之主要是说在香港做纯文学真不容易。他说他写的东西分两种,一种是“娱己”,一种是“娱人”。为了生存,他写“娱人”的小说,写好多不同的专栏,整个五六十年代估计写了五六千万字。但他照样抽出时间写“娱己”的作品,
像《寺内》《对倒》《酒徒》这些都是娱己的作品,也是今天传世的作品。
陈彦瑾:初读《酒徒》,有没有感到震撼?
许子东:震撼倒也谈不上,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读文学专业了,开始比较注意他的意识流技巧,后来思考多的是他跟郁达夫、跟五四传统的关系,还有就是《酒徒》中“一个男人,几个女人”的这种模式。
陈彦瑾:《酒徒》里的酒徒形象,和郁达夫小说里的沉沦者、零余者形象,有什么渊源?
许子东:现代文学开始的时候,两种形象是最成功的,一种是农民,一种是知识分子。农民形象最好的、最早的当然是鲁迅的阿Q,知识分子形象就是郁达夫小说里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郁达夫这些人物形象有两个传统来源,一个是中国传统的青楼小说,才子遇到风尘女子之类的;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人”,如奥涅金、毕秋林、罗亭等等。俄罗斯人检讨他们的国民性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找出一个阿Q,他们找出一个没用的贵族,概括起来是聪明的无用人。这两种人混在一起就变成了郁达夫小说里的抒情主人公。现在,这个主人公到了香港。《酒徒》里的主人公,很多地方像郁达夫小说里的主人公,比方说喜欢看书,比方说喜欢女人,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女人,在社会上处处失败,充分显示了一个文人在商业社会的无聊、无用、无奈。可以说,
刘以鬯《酒徒》的主人公是郁达夫的文学传统到了50年代以后最好的继承者。
陈彦瑾:《酒徒》里有一句话:“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这句话也被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引用,而且刘以鬯先生去世时王家卫在微博发的悼念文里只有这一句话。这句话究竟要表达什么?
许子东:很简单,就是记忆有生命力,记忆里面带着感情,带着很多潜意识。但最主要是他的表达方法,这种方法钱钟书说过,叫做“通感”。记忆是一个抽象的词,潮湿是一个可以接触的感性的词。通感就是人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它们在诗歌里面会互相串来串去,这是一种从古就有的诗歌的手法,钱钟书有专门的文章讨论。所以,这句话意思很简单:记忆是有生命力的。很多时候表达的意思并不重要,表达的方式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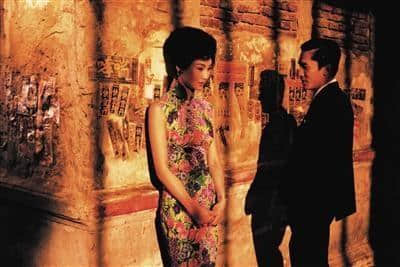
花样年华(2000)
刘以鬯是香港文学与五四现代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
陈彦瑾:从1918 到2018,百岁刘以鬯的一生可以说参与了中国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怎么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许子东:
刘以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一条就是他是五四(文学跟香港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桥梁。
狭义的香港文学是1949年以后才跟内地的文学、跟台湾文学区分开来的,这个香港文学到后来是以本土性为共同主题的,而刘以鬯在这个香港文学当中是跟五四现代文学关系衔接得最完整的一个,他不是来了香港以后才识字写作的人,他在上海已经开始了文学活动,认识了一些作家,但是他又不像徐訏、曹聚仁、张爱玲那样在上海已经出名,那些作家后来我们不把他们称为香港作家,称之为“南来作家”,而刘以鬯又不是典型的南来作家,他在上海已经形成了他的以五四文学为主的三观,但他还没有非常出名,所以他来了香港以后,他在香港文坛的底层开始奋斗。
我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他是香港文学跟五四现代文学之间重要的桥梁。考虑到195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对五四文学有很多隔断,在某种意义上,
刘以鬯是比五六十年代其他中国作家更能够衔接五四文学神韵的一位作家。
陈彦瑾:这方面能不能举例说说?比如《酒徒》这部小说是如何体现对五四文学的衔接?刘以鬯以五四文学为主的三观,主要受哪些流派、哪些作家的影响?
许子东:《酒徒》里有一段,主人公和一个年轻人边喝酒,边谈文学。年轻人问他茅盾的《子夜》好不好,巴金的《激流》好不好。主人公避开了,没有直接去评价茅盾和巴金,但是他说他更喜欢李劼人,更喜欢端木蕻良。在另外一些地方,这个酒徒表示他更喜欢沈从文,更喜欢张爱玲,他说“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沈的《萧萧》《黑夜》《丈夫》《生》都是杰作”,他说“张爱玲的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
《酒徒》写于1962年,刘以鬯是没有看过夏志清用英文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用中文翻译出来,所以
刘以鬯对张爱玲、沈从文的推荐,可以说是跟夏志清英雄所见略同。
但因为夏志清写了学术著作,刘以鬯是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自己对现代文学的独特看法,学术史上我们都说夏志清发现了沈从文、发现了张爱玲、发现了钱钟书,我们不会说刘以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什么贡献,这是很吃亏的。刘以鬯作为作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主流跟支流的关系,艺术跟政治的关系,等等,都看得比较清楚。
一个作家对文学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已经是比较少了,把这些看法放进自己的小说人物里面,那又更少了
,不过在艺术上,很难说是得还是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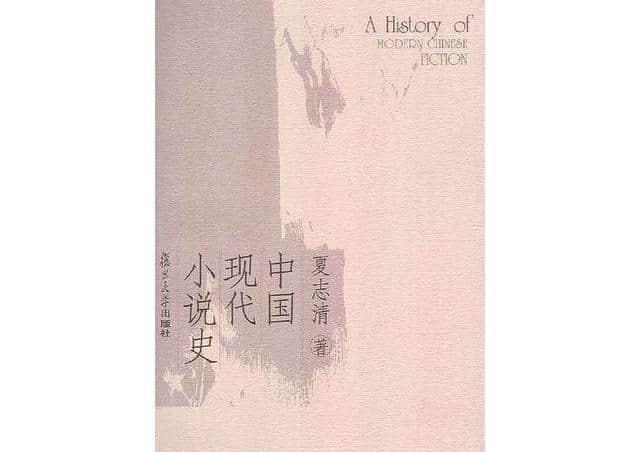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版本:99读书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陈彦瑾:《酒徒》里谈到五四文学的时候,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推崇,更多强调的是他们有独特的style(风格),这与夏志清推崇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原因有什么不同?
许子东:这是很好的问题。虽然他们的结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夏志清更有冷战的政治的背景,而刘以鬯是出于作家的敏感,他直接从文字风格上感觉到这几个作家的独特性,这是他们的殊途,但是他们对于五四文学主流、支流的独特看法是同归。刘以鬯在《酒徒》中说张爱玲有“一种章回小说文体与现代精神糅合在一起的style”,这是非常精准的判断,今天回头来看,张爱玲也的确在这方面有建树。
夏志清错过了端木蕻良,他也没看到萧红。而刘以鬯在《酒徒》中列举的十多篇五四以来的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就有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鴜鹭湖的忧郁》,有萧红的《小城三月》。可惜他都写在小说里了。
你看这哪里像喝醉酒的谈话?他是在很认真地开书单。
那时候的香港大学应该请他去做教授,让他在报纸做编辑真是浪费了人才。
《酒徒》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小说
陈彦瑾:所以有论者说《酒徒》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刘以鬯先生是借《酒徒》言自己的文学志向。
许子东:确切说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小说。讨论小说本体技巧方面反而不是那么多。
陈彦瑾:《酒徒》里谈到小说出路的问题,刘以鬯认为诗歌是拯救小说的唯一出路,所以他试图在小说写作中引入诗歌,把小说当做诗来写,他的这个实验是中篇小说《寺内》,长篇小说《酒徒》其实也是。
许子东:这大概是因为刘以鬯当时看到香港畅销小说的主流都是武侠、言情,都是以情节为主的,所以他觉得他心目当中的
小说要找出路,就要找诗歌体
。当然作为个人追求是可以的,但作为整个文学史发展方向,这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陈彦瑾:那么在您看来,刘以鬯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有哪些?他被誉为“香港文学一代宗师”的理由是什么?
许子东:
刘以鬯的贡献有三个。一个是前面说过的,他是香港文学跟五四文学的桥梁。第二,从他开始了香港文学的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成为香港文学的主流。
这个现代主义比台湾后来白先勇、余光中他们的现代主义要早,比内地198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当然更早。虽然现代主义在1930年代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张爱玲那批作家里已经有一些发展,但是作为一个主要潮流,现代主义在香港发展是最完整的,这方面刘以鬯有巨大的贡献。
还有第三个,刘以鬯主编了一些报纸副刊,像《快报》的文艺副刊《浅水湾》,创办了《香港文学》,培养了一批香港年轻的作者
,包括西西、也斯等人,后来这些人成了香港文学本土派的中坚力量。本土派作家都是在刘以鬯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刘以鬯是“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就是这个道理。
概括一下就是:
第一,他衔接了五四文学。第二,他开创了香港文学的现代主义主流。第三,他培养了不少后来成为主流的香港文学的作家。

《酒徒》,作者:刘以鬯,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刘以鬯和金庸是香港文学最重要的代表
陈彦瑾:在香港,刘以鬯是香港严肃文学的最主要的代表,所以任何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当中,刘以鬯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没有得到充分注意的原因是什么?
许子东:这个原因可能有点苛求了。因为香港是以台湾为出版市场依归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觉得余光中、白先勇的文字都比刘以鬯更Sophisticated(精致),刘以鬯比较多一点五四老派文人的写法。至于在内地,我开玩笑说,主要原因是刘以鬯的“鬯”字太难读了,很多人读不出来。严肃地讲就是,内地的读者包括一般的文学青年对香港文学有偏见,他们知道金庸,他们也很熟悉倪匡、亦舒,甚至张小娴,但是对于刘以鬯、西西、也斯这一路的作家,重视得不太够。
陈彦瑾:刘以鬯的文学贡献跟香港这座城市是密不可分的。有意思的是,张爱玲1952年去香港,三年后离开香港去美国,而刘以鬯1957年定居香港后从此再没有离开。他的作品大都反映香港现实,小说《对倒》就写了1970年代香港街头的庶民生活。对香港,张爱玲是过客,刘以鬯是扎根。张爱玲的离开和刘以鬯的扎根,与他们各自的文学观念有关系吗?
许子东:香港对张爱玲非常重要,很有意思,她在香港的时候一点都不写香港,可离开以后,不管在上海还是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在写香港。香港对张爱玲来说,第一是异国情调,是一种伪西方;第二是一种破落的传统,一种晚清的气息或者说伪东方;第三很重要,是一个冷战的环境。张爱玲没打算留在香港,她一开始起步就是用英文写作的。
刘以鬯无处可去,他必须留在香港。所以他在香港必须通过香港的文化环境来求生,也就是说他不能像我们这样躲在大学里,他也不能像已经成名的曹聚仁、徐訏、叶灵凤那样吃过去的本钱,所以他要编各种各样的杂志,同时他还帮助香港的年轻人。所以,刘以鬯,香港人是认他为香港作家的,而张爱玲、余光中,他们都不认为是香港作家。香港文学这个概念有它非常狭义的保守一面。上海编了一套《海上文丛》,把所有跟上海有关系的人都纳进去了,沈从文也算,梁启超也算,什么人都算。编香港作家文丛的时候,不要说张天翼、萧红不算,张爱玲都不算,余光中在香港待了那么久都不算,但是刘以鬯算,因为刘以鬯全部的文学生涯真的是跟香港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关系。
如果我们要从香港文学找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金庸,一个是刘以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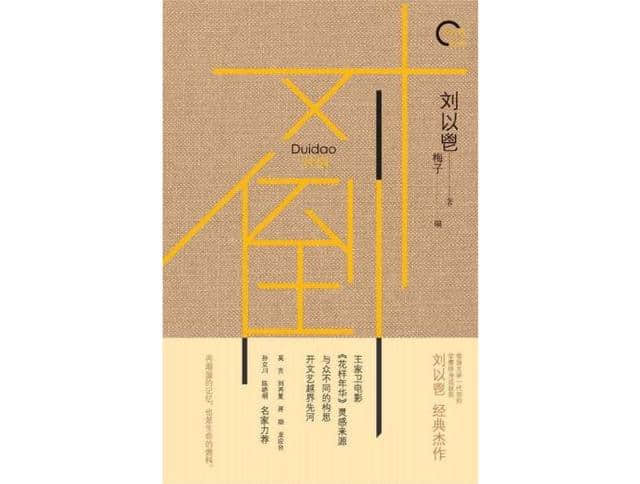
《对倒》,作者:刘以鬯,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刘以鬯是首位用长篇小说进行意识流创作的中国作家
陈彦瑾:刘以鬯被称作是意识流在中国的传人,他的小说写作和乔伊斯、伍尔夫这些经典意识流作家有什么异同?
许子东:刘以鬯的意识流是中国式的,太清醒了,他的意识流不是主人公的意识在流动,是作家安排主人公,或者这样说,他不是人物的意识在流动,是作家安排这个人物的意识流动。比如《酒徒》有一段回忆他的个人经历,每一段开头是“轮子不断地转”,然后带出他的一段回忆。太理性化了。他的意识流不如当时香港一个作家叫昆南。简单说,昆南写的主人公是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真不知道自己想什么。而刘以鬯的主人公是很清楚他要什么,他对香港文学环境的愤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五四知识分子的道德的坚持,都是太清醒了,这是他思想的成熟,却是他艺术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后来内地出现的王蒙的意识流跟刘以鬯是非常像的。
但无论如何,刘以鬯是第一个用长篇小说来尝试意识流写作的中国作家,1930年代的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他们都是写的短篇,而且《酒徒》最初是一段一段在报纸上连载的,想想这个作品生产的机制跟社会环境,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陈彦瑾:所以您觉得意识流有清醒的意识流,也有相对混乱的非理性的意识流吗?意识流必须是非理性的吗?伍尔夫和乔伊斯的意识流属于非理性的意识流吗?
许子东: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可以写很多文章来研究。但是就个别到《酒徒》来讲,我觉得这个主人公太清醒了,而且他这个人像开关一样,一喝酒就可以想一些问题,不喝酒就想其他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刘以鬯先生是不喜欢喝酒的,所以你看他整个小说里边说是酒徒,他根本没有好好写酒。白先勇的《游园惊梦》那种意识流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
但现在的作家不应该受这些概念的束缚,某种意义上,一部作品靠一个技巧的标签也不是它价值的证明,
刘以鬯的《酒徒》虽然从宣传上来讲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但这也(无非)是一个宣传,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此。
很多作家喜欢写他的人物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昆南是这样,张爱玲也是这样。可是刘以鬯的《酒徒》我们看得很清楚,
《酒徒》的主人公三观很明确,三观很正,他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是得不到而已。所以与其说他像西方现代主义的那种孤独、绝望,不如说更接近郁达夫血缘的俄罗斯19世纪的那种“多余人”的痛苦,一种文人在社会面前的无力感。
香港文学对中国传统的新编从刘以鬯开始
陈彦瑾:前面说,初读《酒徒》时,它的“一个男人,几个女人”的模式引起您的思考,这种模式在文学上有什么来龙去脉?
许子东:《酒徒》在描写男女关系方面有一点突破,它开创了一个我称之为“一个男人,几个女人”的模式,这个模式后来在香港文学中一直有遗传。
《酒徒》里面男主人公他看上去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又生活在一个现代都市里面,其实他身上充满了中国文人传统的很多根深蒂固的DNA。
他一共碰到四个女的。一个叫张丽丽,是一个有钱的女的,但最后骗了他。第二个是房东的十六七岁的女儿,叫司马莉,很主动,但男主人公拒绝了她。还有一个是女房东。但是男主人公喜欢的是一个舞女杨露。为什么这么多女的喜欢他?当然这是中国文人的幻想了。但有趣的是,从鲁迅对晚清小说的分析去看。鲁迅把晚清的所谓狭邪小说分成三类,一类叫溢美,就是说写得比真实的更美,比如说《花月痕》里面的妓女跟恩客天长地久的爱情。第二种叫做近真,接近于真实,那就是《海上花》,里面的妓女有好有坏,变成像家庭一样。第三种是溢恶,写得特别坏,特别坏的代表作就是《九尾龟》。对照一看,《酒徒》的男主人公恰恰符合这三种狭邪小说的传统。他幻想的这些女的,张丽丽就是溢恶的,女房东和司马莉是近真的,而杨露是溢美的,完全美化的,可以在风月场中找到纯情这么一种文学传统。难怪《酒徒》的主人公,后来很多人模仿,变成香港文学里面的一个传统。
所以说,刘以鬯的《酒徒》,虽然小说的手法用的意识流,小说的生活背景是一个现代都市,但这不妨碍主人公身上流着中国传统文人的DNA。
陈彦瑾:刘以鬯既学习西方小说技法,同时对中国古典文学也很有研究,像小说集《寺内》里的一系列故事新编,《蜘蛛精》《蛇》《除夕》,有代表性的《寺内》,等等。如何看待这类小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戏仿?他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什么异同?
许子东:香港的故事新编是非常有意思的,它颠覆得非常大胆,这是从刘以鬯开始的。张生不是跟崔莺莺好,是跟红娘好了。后来发展他的文风,李碧华的《青蛇》里,法海是同性恋。大家要是看过陈汗编剧的《赤壁》,林志玲可以跨过长江跑到曹操面前。
香港文学里面有一个大胆新编中国传统戏的传统,这是从刘以鬯开始的。
它既说明香港文化工业对内地传统的看重,又说明他们的肆无忌惮,因为在内地你要这样编,比如陈汗的《赤壁》在内地就被很多人反对,可是在香港无所谓。反过来香港擅长恶搞的周星驰电影到了内地反而被解读成后现代的作品。
说到刘以鬯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潮流的影响,除了他的诗化的语言、意识流的技巧以外,对于传统的颠覆也是很重要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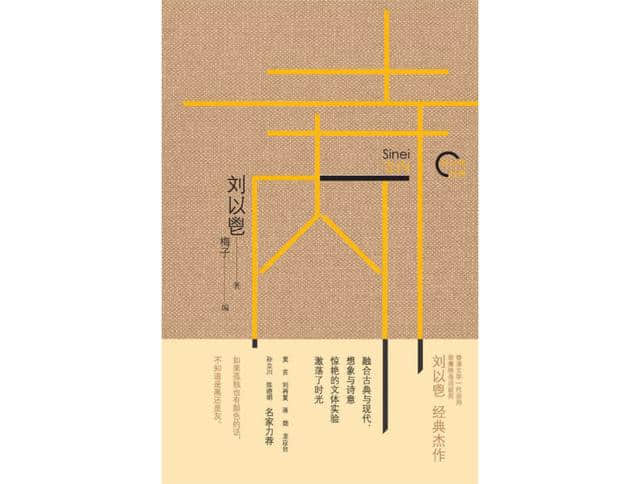
《寺内》,作者:刘以鬯,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
陈彦瑾:但是刘以鬯的小说从文字的诗意、明朗到主人公的三观、情怀和做派,却又是非常传统的,他是如何把现代和传统结合得这么完美的?
许子东:很难说完美吧。完美这个词放到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是承受不起的。我想刘以鬯在构思上比较受西化的影响,但是他在具体的语言上,希望回到中国传统诗词的境界。刘以鬯有一个文学观,他认为写实是过时的,一定要写现代的。当然我们作为评论家不大能够同意他这个看法,写实也可以写出经典的作品,不一定越现代就是越好的。刘以鬯有点文学进化论的观点。但是这不妨碍他自己的探索,他自己的确是这样相信的,他喜欢用创新、探索的精神来写作品。
陈彦瑾:刘以鬯开创的这种写作方法,后来在香港发展的情况怎样?是延续还是发生一些变化?在今天,“刘以鬯式”的书写在华语世界普遍吗?有没有传人?
许子东:前面说过
刘以鬯对香港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主要的是他把现代主义变成了严肃文学的创作主流,而不是现实主义。
香港的浪漫主义都被通俗文学拿去了,无论是武的武侠和文的言情,香港的现实主义写实的作品非常弱,尤其是跟内地来比。但是香港的现代主义写作,很难说哪一个作家具体像刘以鬯,跟他风格比较接近的是昆南。昆南早期的小说《地的门》一点不差于《酒徒》,但是后来昆南也要在香港复杂的文化工业环境中挣扎,晚期作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但是他还在努力写作。西西的风格跟刘以鬯完全不一样,非常理性,不像刘以鬯那么痴情,但在现代主义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具体很难说有谁很像刘以鬯的风格,也很难说他开创的流派有多少追随者。但是我只能这样说,
作为个人,刘以鬯有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从对香港文学的长远影响来看,刘以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也非常值得内地的文学读者来阅读,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当中看,刘以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
整理: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编辑:董牧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