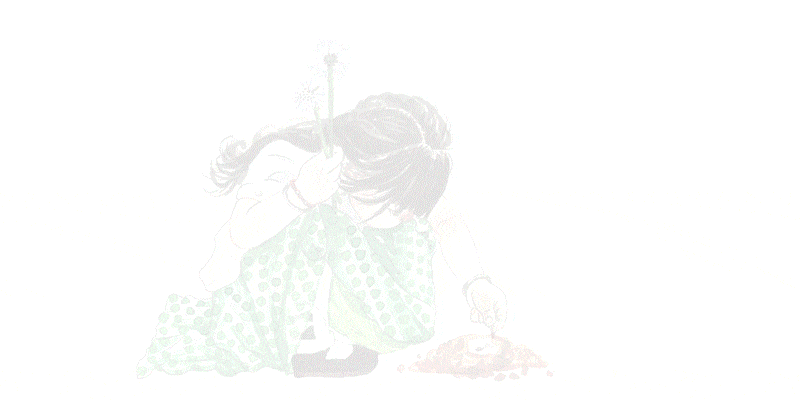 我对二月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对二月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是二月蓝,而不是你们所熟知的荠菜.......
我是出生在祖国西部偏远山区的穷孩子,大约我4、5岁依稀有记忆的时候吧~那时候农业收成不好,每年的口粮都不够吃,我记得有一两年还只能一天吃两顿饭。
到后面记忆丰富起来的上学年纪,口粮勉强够吃,菜也很少有丰盛的时候,当然这里说的菜主要是指含脂肪和蛋白质的荤菜,四川的地理条件相对比较好,一般的菜基本上还是齐全的,何况即使土地大部分都用来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总还会留下一两块地种上辣椒,辣椒酱总是四季都会有的,加上一些储存的咸菜,在菜短缺的季节,依然还不会因为这个苦恼,至少还有辣椒酱或者酸菜烧汤下饭啊,反正每一顿都不会讲究营养均衡,只需要想办法把饭咽下去就是王道。

颖儿姐姐画的诸葛菜~
苦恼的是因为每年的油荤不够吃,虽然过年也杀年猪,但一个猪就200斤左右重,所有的脂肪和蛋白是要供一家人一年的用度,大人们刚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走出来不久,对于这样的生活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于发育期的小孩,却是无法度日的,所以在没有菜的时节,家里大人常发明一种调和的饭,是用每年的储存猪油加上酱油拌新鲜蒸好的白米饭,看上去颜色红红的,又带点肉腥味,以供馋嘴的小孩解解那种对脂肪的奢求和欲望。
记得那时候我吃这样的饭能吃上两大碗,有的时候连酱油都买不起的时候,就撒一点盐代替。家长们给这样的饭取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叫“油油饭”——取两种油(猪油和酱油)相加而成之意。

油油饭~我吃的没有这么好~不会有葱!本图转载自搜狐重庆,特表感谢!
我10岁生日那一年,外婆一个人来给我庆生,那天实在拿不出来什么好吃的给我庆祝,就把家里养来生蛋的一只老母鸡杀了,一为给我庆祝10岁生日,二为招待外婆她老人家。上午要去地里做完农活才生火做饭,通常都比较晚,我又是年轻小孩,哪里忍得住饿,等饭蒸好之时,早已饿得饥不择食,便自己按照往常一样两样油就拌了个“油油饭”吃个全饱,等把鸡炖好端上桌,哪里还吃得下一丁点,大家一抢而光,到晚上连汤都没了.....当时家里人一并都觉得生了一个傻子......

西南著名野菜~凉拌鱼腥草~
所以,在我记忆的儿时时光里,家里人对野菜是很嫌弃的,主要是他们刚刚从吃野菜、吃树皮、吃土(对,真的是吃土)的日子里走出来,就连西南地区目前最喜欢最流行的鱼腥草,都会被嗤之以鼻:那有什么好吃的~

看是什么野菜?
所以更别说什么蒲公英、水芹、灰灰菜了,所谓的什么荠菜在田里、地里一般也长的很好,和鹅儿肠一起,通常倒也是猪草中的极品,遗憾的是当时连名字我们都未曾给过它~直到,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才偶然有一篇课文讲的《挖荠菜》,但由于并不贴近我们的那种生活,索性也就只是知道而已~

这个你们都认识的~
所以,小时候,我,以及我们家人是嫌弃野菜的,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不过时光总是过的很快~到我去南京的时候,已经离学过《挖荠菜》10多年了~社会发展变化大,从小时候渴望脂肪和蛋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变了~从稀缺到过剩了~每天的桌子上,总巴不得有点素菜下饭,才觉得是完美的~
恰好我们研究所因为食堂条件有限,是鼓励学生们自己做饭的(即使没有鼓励,也从未曾见过反对~),离菜市场没有很方便的公交车,打车又太贵~只能骑自行车来回,又由于是朱元璋墓的旁边,当属风景区啦,骑着自行车通常会被来往的车辆挤在白线外面那几十公分的空间里,稍不注意还会来个亲密接触,摔个人仰菜散~所以,对于还是学生的我们来说,买菜也经常成了一个大问题~

所幸的是研究所有3000多亩呢,在很多角落都遍布着各种野菜的资源~鸭儿芹、车前草、苜蓿头、马兰头、蒲公英、枸杞头......我最喜欢的是二月蓝了,在红枫岗的路边,在蔷薇园的墙旁,在实验楼的楼下,在树木园的林下,在蓝莓实验园的路上,都长的满满的二月蓝~在春天的季节里,嫩生生的二月蓝,在静谧的明孝陵旁,陪伴着我们一起欢笑、学习.....在我们懒惰或者因为天气不佳来不及去菜市场买菜时候,还可以作为我们的一道素菜~清香扑鼻,比隔壁芸薹属的那些栽培菜似乎更多了几分回味无穷,同时也让白米饭多一份清香,让白面条多了一丝点缀,让每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腊肉少了一分油腻,我们的生活也多了一份清新和爽快~

在一个人离开西南之地,离开家乡,去往江南孤苦无依的时候,便是诸葛菜伴着我度过那人生中感悟颇多的三年~这种感情是很特殊的~
因本植物在农历二月开蓝紫色花,得名二月蓝,当属名符其实了,但有些地方总将蓝字替换为兰字,查无资料,经过翻阅各个资料,才发现极有可能是因为文革时期推行第二套简体字方案时候的误用,二月蓝有一个大家更愿意称呼的名字为诸葛菜,这名自然是与耳熟能详的诸葛孔明有关的,传说很多,普遍接受的一种是诸葛亮当上了刘备的军事中郎将之时,总监军粮和税赋。有一天,诸葛亮微服出巡,见一种菜,称为“芜菁”,从老农口中得知此菜浑身是宝,叶子和茎都能吃,吃剩的可制成腌菜,青黄不接时,这菜可成为当家菜。诸葛亮对此菜极感兴趣,他向老农问了每亩“蔓菁”的产量及种法,便下令要士兵开荒种这菜,一方面补充军粮,另一方面又可用作牲畜饲料,既经济又实惠,一举两得。后世因纪念诸葛孔明之功,便也逐渐将此二月蓝称为诸葛菜,《中国植物志》收录的中文名也是称诸葛菜的。

由于诸葛菜通常成片生长,从初春开始开花,花期长,颜色艳丽。翠绿的叶丛中点缀着紫色的花瓣,煞是清秀隽丽,又与古代圣贤有关,所以常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咏颂。
宋代蜀中名士李石,少负才名,及第后,曾任大学博士,赋有五律《诸葛菜》一首以赞诸葛菜:“郡圃耡荒雪,家山斸浅沙。只今诸葛菜,何似邵平瓜。小摘情何厚,长斋气自华。官烹与私炙,随处即生涯。”
清人张邵有《诸葛菜》一诗:“扶疏紫翠应炎精,野蔌能将大姓争。花史标堪垂不朽,草庐中岂傍先生。分丛尚托躬耕意,匝地空留割据情。已见敷荣遍吴魏,蜀都赋里不须名。”
清代陈作霖曾作一词《减字木兰花·诸葛菜》:“将星落后,留得大名垂宇宙。老圃春深,传出英雄尽瘁心。浓青浅翠,驻马坡前无隙地。此味能知,臣本江南一布衣。”
这些诗词多多少少寄托了作者对诸葛菜和诸葛亮先生的感情在里面~诺诺本是一俗人,但有时候会去读这些优雅的诗词,或者想古时那些优雅的圣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徘徊思绪间,又增加了另一种超越生活之外的对诸葛菜的特殊感情~

将诸葛菜写的最唯美朴实的文章,当属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散文《二月兰》,此处仅摘抄部分,以免各位翻阅查找之苦: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制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蓦地发现,从我住的楼旁小土山开始,走遍了全园,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用得真是无比地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以上便是季羡林先生描述的诸葛菜团结起来一起开放的那种美~大写的美吧!
不过对于诸葛菜的美味,季老先生却未曾品尝,因为文中有一句提到老祖的时候说: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旁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

这荠菜饺子,也可以换成诸葛菜饺子的,我保证味道也不差~
想来,荠菜在北方作为野菜确实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连季老先生家都是在诸葛菜丛中去搜寻荠菜,不过在对诸葛菜有特殊感情的我看来,不免觉得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喜欢挖荠菜的人大多是用来做荠菜饺子,始终觉得荠菜饺子好吃是因为饺子好吃,而荠菜的功劳,换个猪肉白菜饺子也一样好吃,尤其在《挖荠菜》的年代,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诸葛菜则是响当当的做菜啊,或者谁用诸葛菜包饺子,说不定味道也是极好的~
荠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当属小时候读书学过《挖荠菜》的课文罢了,把挖荠菜换成《二月兰》,或者诸葛菜恐怕早已名扬天下了~

不过不管是荠菜还是诸葛菜,还是其他什么菜,只要是野的,现在都很有市场,像《挖荠菜》课文的结尾一样,我们也希望朋友们珍爱荠菜,珍爱诸葛菜,珍爱野生植物资源,珍爱生活,自然条件好了,大家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本期供图:金缕梅/安静/小强/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