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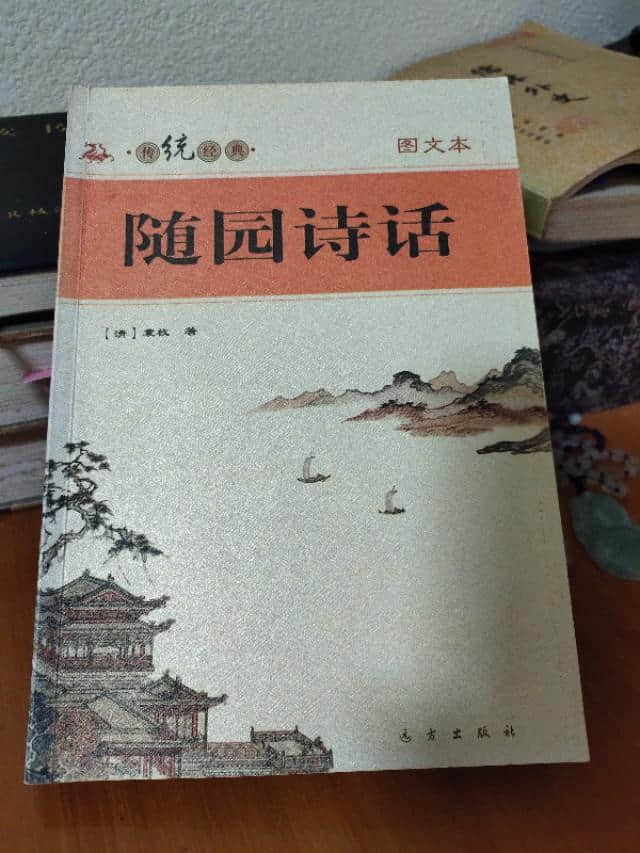
格调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虽然必不可少,却也容易制造。何况它带有很重的技艺性,一方面门槛低,另一方面,若着意经营,则势必由“空架子”走向“花架子”,为形式而形式,甚至成为“绣花枕头”。“风趣”是一种“意味”,犹如一盘佳肴呈现出的独特的色、香、味、形的总和。光有“架子”没有内容即“佳肴”,“意味”是产生不出来的。然而,“佳肴”的创造非高超的“局掌师傅”莫属,没有这一领域的天分和才气,恐怕连其皮毛也摸不着。
文学创作的主体,必须具有浓烈的真情、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灵性,这样才能写出性灵,也才能使作品呈现出真善美的风趣。什么“诗教观”,什么“格调说”,什么“肌理论”等等,都未能揭示出文学的这一内核。
2.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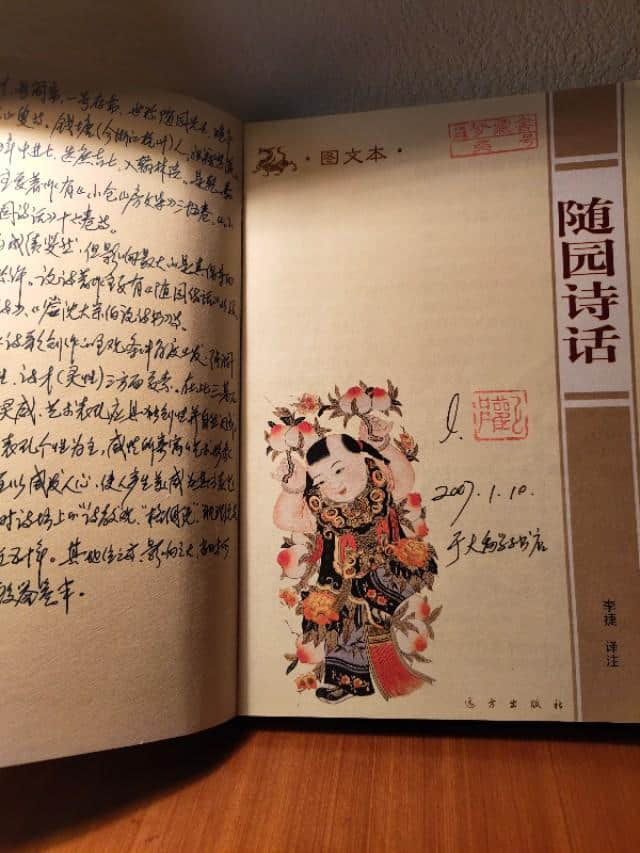
此乃袁枚对普天之下“文学爱好者”好心的告诫。舞文弄墨脱颖而出了自是风流,极易浪得虚名,有的还可因成功“立言”而被青史记上一笔,但这只是其好看的一面。另一面,则犹如一幅至美油画的背后一样糟糕。“作画”过程中苦行僧似的清贫乃至潦倒,哲学家似的绞尽脑汁想破脑壳,探险家似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即便如此,假若独独缺少一种宗教般的献身精神,那依然是难以在文苑里占有一席之地的。
笔者庆幸尚有自知之明,连做梦都没想过当作家。之所以能坚持给文学当票友至今,是抱定一个“快乐读写思”的信念,只求“读写思”的过程快乐,不求“读写思”的成果高下多寡。不求正果,唯求快乐,“年年不空过,日日有小酌”,自然也不求名不求利。对于文学这个令吾辈又爱又恨的尤物,充其量只是把她当情人,把写作当做“快乐人生”的一个手段与途径。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是人不是人,都在搞散文;是文不是文,都在叫‘散文’”,我是不大感冒的。因为这在浪费社会资源(包括媒介传播资源和人力财力资源),浪费追求者的才力精力以及宝贵的人生。
“吟诗”一需才气与性灵,二需安贫乐道孜孜不倦,以致使出浑身解数、献出毕生精力。光凭勤奋刻苦与矢志不渝,极难登上象牙之塔。因此,奉劝绝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平凡人,文学风情万种,可爱却很“酸”,千万不要被她所迷惑;假若自量没有文学创造的天分,没有准备好全副身心追求她并托付一生,千万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选择走这一条不归路。
3.大道得从心死后,此身误在我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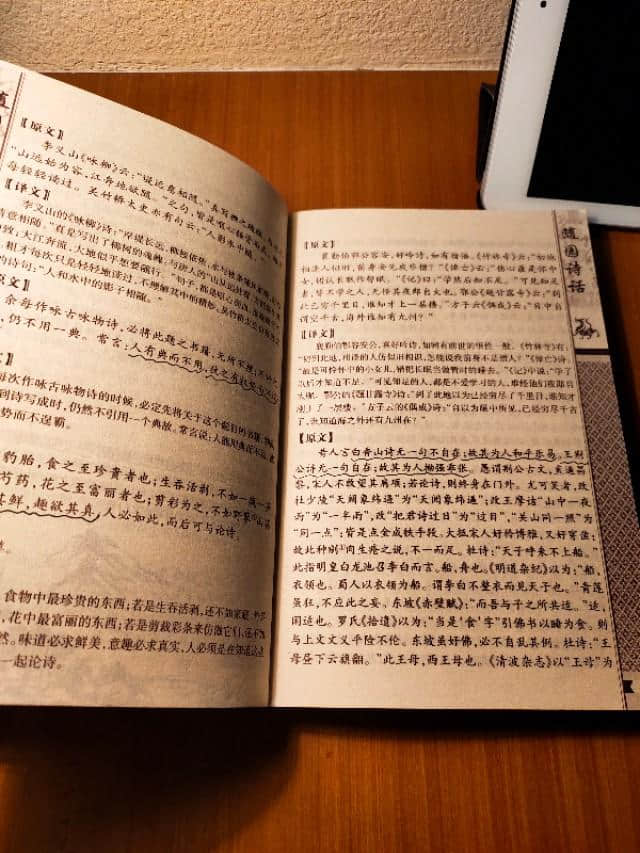
对于悟出了“文学既要天赋又要托付终生”禅道的文学爱好者,其得道之时,实在就是其文学之梦的心死之日。换句话说,得道之时,即是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之日。得道越早,耽误越少。“生前”耽误了的,“生后”还来得及弥补。人生价值并非唯一体现在文学创造上。世上的路有千万条,从文仅仅是其中最为清苦最需天分且最为拥挤的一条,其它的条条大路都可通罗马呢。
选择文学这条路,事前真的要想清楚。
4.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如今的多数作品恰恰相反,能够用典之处拼命用典,唯恐读者误以为作者胸中无典。我个人常吃降压药,把原有的可怜的记忆力给降得所剩无几,因而我确实是读者担心与小觑的胸中无典之人。可这并不能代表多数搞文学的情形啊。其实,作者与读者都不要怕无典,只要作品的文字背后有典即可。此即袁枚老先生号召的“人有典而不用”,实乃人有尊严不怒自威也。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杖人多笑,十里珠帘半下钩

用典于作者,犹如人老簪花,不仅见者多笑,而且花也会因上老人头而自羞的。舞文弄墨与其他行当不同,其他行当的“作品”也许愈显花哨愈好,文学作品却是最为推崇质朴无华的。俗话说的“满罐子不荡浅罐子荡”,正好是文学之华与实方面的真实写照。
6.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则任事有余;志小,则愿无不足
谁都希望自己才大,这点没有异议;问题是谁也不冀望自己志小。志之大小,其实没有标准,关键是要与自己的才气相符。“志”乃“衣”,“才”乃“体”,量体裁衣是也。志小则“愿无不足”,挑明了这个利害,相信作者诸君便会明智地选择量体裁衣而非好高骛远的。
7.蝉移无定响,星过有余光。送迎人自老,新旧岁无痕
蝉移无响、岁逝无痕,星过有光、人过自老,自然界与人类的诸多现象及定律,都是值得文学创作学习借鉴的。本来,文学创作的主要功能,就是真实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变化;何况,文学作品追求形象逼真的同时还得追求生动传神,那就更要从自然与社会的客观存在中吸取源泉。本质的外表多是质朴,泡沫的外表才是花哨,舍本逐末恰恰是弄巧成拙的“大愚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