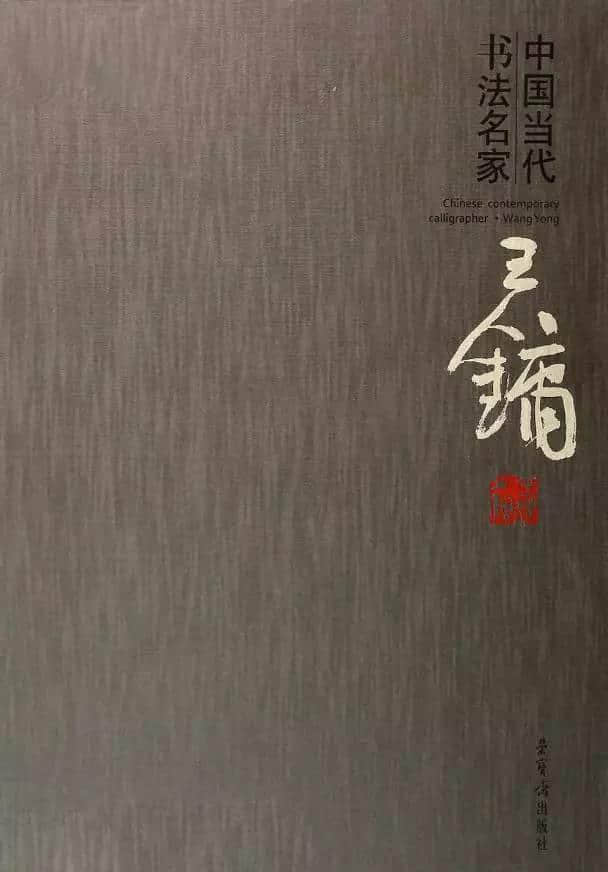
读阅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书法名家•王镛卷》,便被一种莫名涌动的力量所鼓荡,反反复复,不忍释卷。
继而,一些与“王镛”有关的词汇便浮泛于脑际:流行书风,民间书风,艺术书法,中国书法院,央美书法系,等等。可以说,近30年来于“书法”领域最沸沸扬扬的争论,似乎都与王镛不无关联。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值探讨。
其一,书法与写字的问题。
以笔者浅见,王镛之于“艺术书法”的提法,实属“无奈”的一个命题。
虽然“艺术书法”的目的是强调艺术性,但事实上“书法”本身就包含有“艺术”的成分,只不过,原本明明白白的道理于今似乎不再明白,不“看图说话”一般摆出来,似乎我们的思维在任由二者的概念混淆。
艺术就如一座金字塔,你站在哪一层面决定了你的审美判断及艺术水准。不站在一类高度上面,你所望见的景致注定不同。所以,艺术的审美应该也有所谓的仰视、平视与俯视之别。说是提升艺术的高度,走进艺术的深处,实际上对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愿望,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你自认为走了进去,但或许只是在门边转过一圈而已。
当然,从几案之间走向墙面,从居室走向展厅,书法从原来的实用性为主走向了“单一”的艺术属性,从少数“贵族”阶层所独享到不分等级的“全民运动”,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书法该何去何从?是直面诺大展厅的挑战,还是抱残守缺式的自娱自乐?记得美国画家德库宁曾说过一句类似“我的画就要在展厅里一下子跳出来”的话,表明了一位现代艺术家在创作上敢于面对专业展示空间的勇气和信心。——我们对此是否有所感触?
可以说,当今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审美也自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王镛所倡导的书风,正是这样一个与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相伴而生的产物,它绝非某些评价的所谓以鼓吹“民间书风”来“否定经典”,而是要对古代的文化遗存做重新评估,择其善者而从之,是回归书法本体,探讨当代书法该如何去摆置,如何去充满,如何去“照亮”展示空间的问题。它注定不会尽善尽美,注定会伴随着泥沙俱下的局面,但那种心灵跃动的创作激情不可遏制,那种体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人的创造力与聪明才智得以真正发挥。
其二,关于“美”与“丑”。
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曰:“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明末傅山提出“四宁四毋”的艺术主张或由此来源。当然,傅山更肆无忌惮,将“丑”也直接拉进来,创造性地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关乎傅山的价值观与美学观:即使“拙”了,“丑”了,也不能“巧”和“媚”,而“拙”与“丑”正蕴涵着深层意义上的高雅。
实质上,道家思想中对“美”与“丑”有辩证的分析,如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庄子》认为“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如对王骀、申徒嘉等形体丑怪的人评价:“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又说“西施病心而摈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以及“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作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等等。西方文艺于此也有类似表达,如罗丹说,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再者,于今看来,杜尚之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丑”的小便器的粉墨登场,更像是举起了一杆针对架上乃至古典方式的祭旗,看似大逆不道,呵佛骂祖,却撕开了陈腐积习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从而打开了艺术真正走向现代的一扇门。
可见,有时“美”中能见“丑”,有时“丑”中可见“美”,“美”与“丑”并非绝对化,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世间万物,日久生情,或者久则生厌,都说明这样一种可能的互动。甜点诱人,但一直吃下去,可能会让人恶心,甚至就坏了胃口;粗茶淡饭,似乎寡味,却给人以持久的、实实在在的味觉体验。水晶球玲珑剔透,令人惊异,却不过工艺意义上的“器”之雕琢;土陶粗糙简易,不受瞩目,却或许深藏一种高古、质朴之美。
有人认为,自宋元以来,中国书法在逐渐走向衰败,但事实上却是一个是书家们在遵从认知自觉、持续寻找真我的过程,是让创作者的心性与个性不断得以展现的过程。所以,诸如杨维桢、徐渭、傅山、八大、金农、龚晴皋、徐生翁等人的演绎,为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视觉空间,这个空间或许狭长,或许陡峻,但足以启发我们: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审美之外,分明还有一块别见洞天的世界。
王镛曾在早期的篆刻集自序中引用了吴缶庐的一句话:“小技拾人者易,创造者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毛皮矣。”可以说,王镛自始至终以此自励。他曾谈到:从艺方向的明确,审美观的建立,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独到判别,是形成自我艺术风格的前提与关键。而其于习艺之初,经启蒙老师的引导,便确立了“以古拙质朴、奇险壮丽为大美”的审美定位,并自信“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东西不好,整齐匀称不过是美的低级阶段。”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可以说,王镛遵循的正是一种至朴、大美的道家美学观。无论对民间性的汲取,还是他创作上对“大、拙、古、野、率”的探求,均体现了一种“大巧若拙”的审美理念与大美无华的精神境界。
其三,多能与专擅的问题。
现代艺术教育的特色,往往以图像的塑造能力为前提。所以,技术层面的训练成为重中之重。由此,“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的认识,变得顺理成章。然而,这恰恰与中国文艺的修为方式不无偏差。中国文化讲究综合性,讲究广取博收,天长日久,如文人画之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修为,讲究多方面知识修养,尤其表现为诗、书、画、印四位一体式的融通性。所以,数点中国画的历史,似乎也是画家们一步步从“专擅”走向“多能”的一个过程。
“对于从艺者来说,当然是基础愈宽,则能力愈强;变数愈多,则出路愈广。”王镛如是说,尤其是“书、画、印三门艺术都是以传统的点线审美为基础,以点线的组合构成形式为表现手段的、独特的民族艺术。”“三者的本体艺术语言是一致的”,“孤立地研究学习其中一门,是很难取得大成就的”。基于这种认识,王镛始终保持着文人画家修为的传统,延续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集诸艺于一身的艺术养成方式,注重诗、书、画、印等多方面的积累实践,其书、画、印创作虽形态各异,但在风格上、意境上,却表现出自然和谐的统一性。
其书,于六朝碑版,汉魏简牍,砖文瓦当,无不着力。在注重章法的同时,也讲究字形、字势的形式美感,笔下形成一种充满现代感的奔放不羁的风格;其印,三代铜鼎,秦汉古印,明清流派,无不涉猎,集而创具一种古拙奇崛之印风;其画,则将书法骨力与金石韵味统和于一,以书入画,强调点线的书写性,追求沉雄朴茂、大气磅礴的画风。
其四,关于“传统”与“创新”。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艺术具有广泛的包容与涵盖属性,允许无限的创造力来塑造。而艺术史的形态,注定是一个不断检验人类智慧与能量的过程。所谓创作,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创作者不断观照以往的经典,但这不是终极目的,而是要从中总结规律和经验,分析优劣,酝酿创生的可能。
传统是一条河,一条流动的河。既然流动,就是鲜活的,活跃的,是奔涌不息的一种状态。昨日优质的内容积累下来,形成稳固的河床,而平缓与激荡的塑造,却在于河水的流量与冲撞的速度,场面自然千差万别。传统,是需要不断创造着的。昨日的创新,成为今日的传统;今日之创新,正可为明日之传统。当然,过去时代里的优秀,也可能成为今日的过时。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浪淘沙,经得历史的淘洗,才能见真知。
一种新生事物,往往伴随着撕裂与阵痛,往往惹得故有老派的瞠目,这,也是情理之中。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有固守一隅、自以为是、保守不化这样的词汇创生出来。毕竟,积习也是长此以往叠加起来的,只不过,我们对待传统的方式,更习惯于轻车熟路,更满足于习以为常。
近年来,中国书法界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民间书风的冲击。然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人欢欣鼓舞?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批判”而这些家伙至今仍不知悔改依然乐此不疲?
答案只有一个:审美与心灵有所共鸣。
回顾一下,清中叶的碑学兴起,是伴随着帖学衰微、金石之学大盛而乘势发展起来的,如阮元、包世臣对碑学的倡导,到了康南海,更是高调鼓吹“尚碑”,甚至对帖学一系予以全面否定,这固然比阮、包更猛烈,更偏激,却真正使碑学得以大大促进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二百年的境状波澜起伏,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间意识形态的局限,改革开放后“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创作本体的觉醒,文艺领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思潮,事实上书法的发展与这些因素都是分不开的。
王镛之于民间书风的倡导,提出以“根植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为宗旨的“流行书风”(只是一种提法),实际上更为注重感性发挥与理性自觉的互为补充,这绝不仅仅是对古拙、朴厚、粗犷审美风格的敏感与认可,更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是对清末“尚碑”理念的一种演进和深化,是当代书法之所以不愧于时代的一种认知觉醒。进而,在当代书法发展史上,碑与帖,经典与民间,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诸多因素,都成为可以自由穿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合法公民”,各具特色而多元共存。
应该说,王镛及其艺术,是以探究艺术本质为旨归的,他所追求的深山大味,他创作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元气淋漓障犹湿”的从容气度,无疑是于“错彩镂金”与“清水芙蓉”之外的另一阐释,无疑给现今这个信息迅捷的时代,开拓出了一个意象苍莽而气象鲜活的审美世界。读其书法新著,似乎随着那点画与线条跳荡着的风神气韵,踏上了一次重新品味原始、重新回归民间的精神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