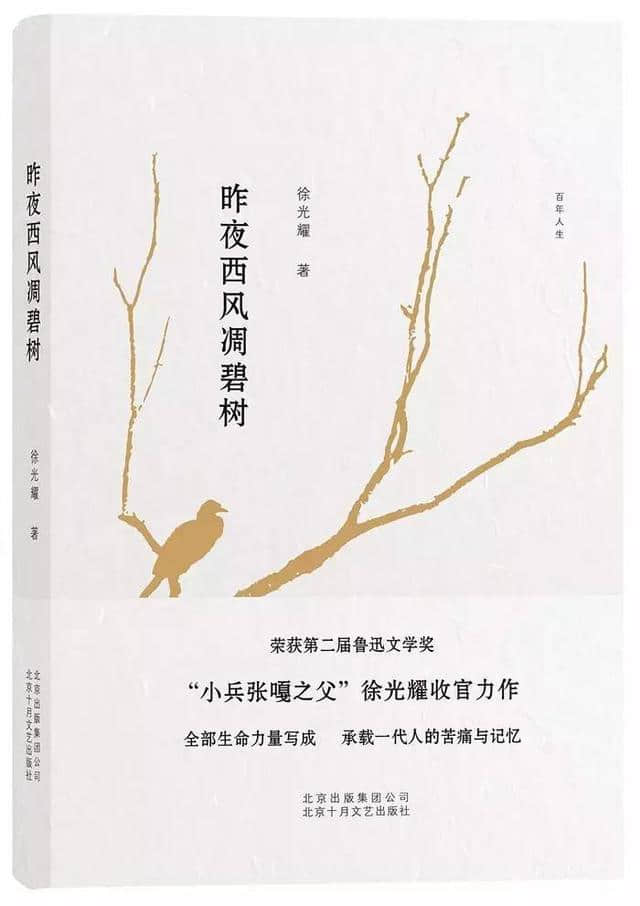
回顾我的一生,有两件大事,打在心灵上的烙印最深,给我生活、思想、行动的影响也至巨,成了我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这便是抗日战争和反右派运动。
抗战八年,可以说,无论什么罪——苦、累、烦、险,急难焦虑,生关死劫,都受过了;熏过一回毒瓦斯,还落在鬼子手里一次,但都闯过来了。大背景是全民受难,大家都奋斗,都吃苦,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个人星点遭际,有什么值得絮叨的呢?
然而,永远难忘的是那些浴血英雄,是那些慷慨捐躯的烈士。他们没有计较过衣食男女之事,没有追求过功名利禄之私,即使死去了,也没给自己或亲族留下私财私产,最后拥有的仅仅是祖国大地上的一黄土!可正是这个赤条条,才显出他们那牺牲精神的纯洁神圣、伟大崇高!如果说人性,还有比这种人性更高尚的吗?
我是个幸存者。我幸存而且分享了先烈们创立的荣光,靠的就是他们用破碎的头颅和躯干搭桥铺路,奖掖提携,使我熬过来了!以此之故,我的绝大多数作品,我的主要小说,都是写他们的,特别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那民族灾难的深重,那残酷艰险的极至,都大出人们的想像,所以,我的一部长篇、三部中篇、一集短篇中的大部,以及我四部已摄电影中的三部,都是写这次“扫荡”的。除去它们,我几乎就没有了作品。
这就是我的抗日“情结”,是我这个人的主要侧面之一。
反右派运动之所以成为我的另一“情结”,就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中年以后的命运。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尽管很难相信,却眼花缭乱,迷迷糊糊。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又几经天旋地转,才慢慢有点明白,于是忐忑地、间隔地写了几篇文章,这便是十多年前所写《我的喜剧》系列。直到过了七十岁,已入沉沉暮年,时常听到人们对“阳谋”现象的研议,才又有些新的感悟,《昨夜西风凋碧树》由此形成。所有这些,从本质上看,都是反映着我的“反右派情结”的。
我以为,“阳谋”之所以比阴谋更可怕,就在于它的“阳”。搞阴谋,是必须蒙蔽阳光,躲人耳目,弄些遮饰手段,并在暗箱中操作的,其影响作用当然大受限制。而“阳谋”,却能凭借官权之威,领袖之望,向全党全民广发号召,大作动员,乃至公开抛弃道义,驱赶人们自投罗网。那些单纯赤诚、忠心无二的后生小子,甚至不经任何思考,便信实而上钩了。倘不用“阳谋”,何至如此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而“文化大革命”,益发变本加厉,如法炮制,这才酿成了双倍残酷的全民族空前浩劫。数十年沙场征战、谙于政争的英雄豪杰及无数才俊,不但不能反抗和阻止,且眼睁睁地一个个纷纷跌倒。此情此景,尽管已过去了二三十年,仍不能使人们的记忆有任何淡化。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下半截,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而“阳谋”,与我们党的宗旨和性格,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刚刚崭露头角的“失败学”告诉我们:如果对失败粗心大意,不去认真总结和记取教训,那么,“严重事故”继续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乃至“重演”。所以,我们对个人迷信,对封建主义,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必须时刻严肃地警惕它,揭露它,扫除它!既要不厌其烦,又须有股子缠磨劲头,一直缠磨到伟大的五四运动所提目标的彻底实现为止。
我的两大“情结”,前一个是自愿养成的;而后一个,则是被迫形成的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论阴阳,如果后一“情结”是“阴”,那么前一“情结”便该是“阳”。倘不与“阴谋”、“阳谋”相混,而使阴阳合一,那便是我这个具体的人了。知道这一点,对了解本书和我本人,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此书主干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自今年年初发表以来,半年间,接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或电话,有八十余封(个),多数表示了勉励,除《长城》上有十五篇“笔谈”外,由刊物和报纸加给的相关按语,也有五条之多,有的按语甚至说,它“在文学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实出我之意料,连我影响较大的《小兵张嘎》,也不曾获得过如此赞誉。于是朋友们督励我:“乘势追击”,把“故事”继续往下写。他们以为,党外生活二十年,当有更多的“戏”好看。
其实,我在前十多年写的《我的喜剧》中,有不少篇章,便是对那阵子“党外生活”的回忆。但由于每篇一题,每题一事,中间缺乏串联,未成体系。加以写时心境时变,情绪不同,还有时开点玩笑,杂些点染,有的读者便把它们当做小说来读。若究其内涵,无一不是作者亲历亲见,与《昨夜》一文实是一脉相通的。试看那些精妙的情节,岂是我这等笨拙机械的头脑编造得出来的?这次,便把它们加工一番,作为人生纪实,权充“故事后面的故事”,以为本书添一点“新鲜”和“复杂”。
在前面提到的朋友来信来电(话)中,也有对《昨夜》的批评。如一位朋友说:“前面写的还可以,只是后面不应那样写。”语气颇平和,让人感动。但似乎言外还有意,未能把话说完。于是我想,在那文的结尾,我曾郑重声明过,全篇文字之用意,只在最后那段话,此外“岂有他哉?”不这样写,又该怎样写呢?还有另一位同学,劝我“站得更高些”,当然一片好心,但经思考之后,我只能苦笑:我怎能自甘堕落,不愿站高呢?可我也就是刚从趴着的状态跪起来,身子还不曾站直,如何会站得更高?同学的好心实在让我勉为其难了。
至于全篇文字,也略有增删。经朋友们查对指正,原文中有些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都据实改过了;有些因我之粗枝大叶,没有说清或说准的,也逐一补正过来。我很知道,读者朋友们是喜欢真确的,也只有真确,才能引起真正的信服和愉快。近日有位年轻的同学,写文章评我是“生活型作家”。很对,我很乐意接受,就算是“记录生活”或“照抄生活”吧,也并非对我的贬低。自学习写作以来,我一直信奉:生活是第一性的,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至于缺乏联想和哲思,只要我活着,当然要努力充实补足,但那毕竟是第二性的。
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他们的精心精意,使此书得以出版,这也许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本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