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很难写,能写得好且又好读,更是难上加难。孙德鹏老师的这本《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6—1915)》做到了。这是一本章太炎评传,评的是作品,传的是人生,好在仍有意气挥洒,且不失雄强,或可称之为太炎先生的隔代传心之作。
萦绕此书的不是重整山河的热烈乡愁,而是重启记忆之门,与太炎先生一起走过二十年的天真与感伤:从《訄书》《中华民国解》到《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之后融入了《齐物论释》,融入了鲁迅的平民性、农人傲骨,最后,在《破恶声论》《阿 Q 正传》《孤独者》中,师徒二人雄赳赳地联手打败了时间。
作为一个研习法律史的教书匠,作者执迷于章太炎的一枝热笔,倚着两扇空门,琢磨着 “士别三日” 样的问题:
章太炎人如其名,有一双火眼,游侠气质的火眼,这双火眼是如何观望中国的法律变革的?章太炎是谜一般的革命家,学问好,又有佛学的底子,每以道家文体,写出佛家慈悲,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格?
章太炎迷恋旧时文化,仿佛一个落难的富家公子,隔着玻璃窗望见别人在自家旧宅宴乐,总怀着深刻的尊严感。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知识人阶层常有的尊严感?
章太炎不是在浇水,而是为革命之花浇蜜。人称 “章疯子” 的他每每故做不同,其实是真正不同。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有时间,有精力,有自由,却舍不得拼命,舍不得疯狂,是不是有必要琢磨一下他的疯魔?章太炎从未获得一个所谓的 “官身”,如他所说,打破书斋,只能慈悲地打破它。阅读此书,就是与章太炎一起慈悲,一起来打破自己心上的冰山。

他
眼中的自己
章太炎最让人欣赏的不是丰满的学问背景,也不是宗教式的道德观,而是只要他存在,我们就可以在他的书页里面,与他一起愤怒,并且欣然地接受他那无法遏制的愤怒: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
…… 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
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他们
眼中的章太炎
“读其文,真巨子也”——谭嗣同

1921 年 5 月,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了章太炎。芥川始终以 “先生” 称呼太炎,为这位 “王者之师” 的雄辩所吸引,甚至忘记了抽烟:
章炳麟先生的书房里,不知出自何种爱好,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这间放满书籍的房间,可是名副其实的彻骨寒冷。”
——【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 · 第三卷》
…… 他的相貌并不堂皇,皮色发黄,髭髯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头,看来好像生了瘤似的。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那双在上品无框的眼镜背后,总是冷然微笑的细眼。
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虽曾把先生监禁,却终于未敢杀害…… 章炳麟先生接连地摇着长指甲的手,滔滔然陈述他独特的议论,而我却只觉得心中寒冷。
——谢樱宁在《章太炎年谱摭遗》引述芥川龙之介与鲁迅的会面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先生)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 “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 “××” 的 ××× 斗争,和 “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 的 ××× 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末编》
编者注:
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
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今年是鲁迅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两人皆于1936年去世。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先生初从上海西牢放出,避往日本,觉得光复一时不易成功,转而提倡国学,思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其意甚悲,亦复可感。
国学讲习会既于神田大成中学校开讲,我们几个人又请先生特别在家讲《说文》,我便在那里初次见到先生。《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
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贡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
——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 94 期,1926 年 8 月。

我感觉到,章太炎的思想,在当时的革命中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它,不能成就革命,然而没有它也不能成就革命,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正如他在《播种》一文里引用《墨经》的话那样:“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他在不能指示光明前途的黑暗情况下,只鼓励人人恢复主体性反抗压迫,尽力打倒清朝即压迫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的障碍物,实际上的结果是放人人到新的地方去。
——【日】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2 期

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5-1916)
引言:章太炎的位置
鲁迅视之为 “师” 的,一位是藤野先生,另一位是章太炎。
1908 年,28 岁的鲁迅在东京师从章太炎习 “小学”,上课的形式是专为八人开设的特别课堂,可以说是秘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完全被征服了,终生执弟子之礼;他眼中的章太炎如火般令人神旺: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作为 “独行孤见的哲人”,章太炎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文字艰深的经学家,是流亡的革命者,也是第一个放弃使皇朝近代化念头的 “保守分子”,更以众多 “独怪” 的雅名绰号闻名于世:“有学问的革命家”“清学殿军”“民国祢衡”“章疯子” 等等。
革命之后,章太炎 “自藏锋芒”,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作为一个从革命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他是 “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鲁迅:
到得今日,章太炎几乎成了青年一代不敢轻易触碰的名字,难怪鲁迅用尽最后几分气力纪念章太炎后,又写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说:“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
这篇文字是鲁迅那支 “不卖之笔” 留下的最后墨迹,他是必定想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后,仍有青年耐着性子读起了《訄书》,他更加想不到的是,这个青年仍存有几分满人的血脉。
鲁迅的重要性在于,他以极具穿透力的文字为民国世界画像。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古怪而哀婉动人,有些一事无成却满怀热情。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尊严感,然而宿命地只能是做不成好事的好人。
现在看来,这些典型的鲁迅式的主人公已是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他们的不幸在于,对于这个重负是既卸不下,又担不动。他们离开家乡亲人,独自承担着巨大的时代重负,并且始终摆脱不掉那个时代特有的道义上的痛苦。
这些人是中国式苦难的承担者,也是中国不至沉沦的好兆头——如果真有所谓自然法则,那么这个自然法则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让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在喜爱歌利亚的时代,拥戴钟情于柔弱的大卫更值得称道。
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字,章太炎就只是一个幽灵般、个性怪异、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他的革命热情与他对同代人作出的有限诉说之间有一个落差,由此而生成瀑布般的隆隆回响,每个溪流都闪烁着多重意义。
这个落差几乎成了章太炎所有作品的不变风格。他并不想创建尺度,而是让一切都变幻莫测,然后再锤炼出光辉灿烂的秩序。他比其他革命者更致力于发现被遗弃的文化王国,每部作品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是令人战栗的发现之旅。
为时代画像,难在画出其 “静”。民国是尚未完工的,章太炎使这个民国看起来更像陌生之地,却流露出一种未完成的大气。各派势力持续不断地汲取好处,成为官僚、政客、军阀、学匪,他们无法与革命风暴的中心保持适度的距离,也无法与新兴的领袖保持距离。
章太炎宛转来到中华民国门前,徒然以一支软笔为众生创造出一种需要:一个能适度保持距离,能停下来思考的 “朦胧地带”。在这个地带,人们可以对政治、对领袖有一种生疏,相敬如宾。仿佛立在中华民国门前,才如此分明地确证自己的位置。
章太炎的思想有单纯的一面,就是一片爱、一片赤诚、一片感叹,简单到极点,如一心向往好收成的农人,日复一日,信仰不变。我们可以用 “明日复明日” 来诠释农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为章太炎画像。
唯有语言能穿越时间空间,多次变形之后,仍是失意者高贵的仆人。
作为古文学的典雅继承者,章太炎的文字形成了他的第二重生命,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第二重生活。文学的语言不仅有一层意思,还有多重意思,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丛林。章太炎的魅力恰如深山密林,层叠多变,时而缥缈,时而恳切。
他的文字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那些疯癫的作品才从未丧失力度——质疑这个世界的力度。而能理解这种魅力,为太炎先生伸展遗志的,恐怕还是与他有深刻的 “精神血统” 关系的人,具体而言,一定是那位奉托尼学说、作魏晋文章的鲁迅先生。百年来,对章氏盖棺定论的话正是来自他追忆先生的一篇小文: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
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
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 “中华民国” 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是有别于革命家的革命家,是反对宪政的宪政主义者。他不生产共识和妥协之物,而是疯狂地独断。他对中国的爱是基于熟知,对中国的反思批判亦是基于一种熟知。
不像某些知识人,自己过着好日子,却把世界说成是病房,只知巧妙粗俗。在当时迷恋 “进步” 的汉语圈中,章太炎却不遗余力地主张打破革命的虚妄,打破宪政的虚妄,打破议会的虚妄,打破进化论的虚妄。
当所有人都快要溺死在狂热的革命海洋里时,章太炎的执拗仿佛就是木筏、灯塔、沙滩。
作为汉文学的传承者,章太炎以奇异的姿态将中国思想的古老灵魂加工成未来的革命质料。不过,章太炎也因此备受质疑,“罪行” 是文字太晦涩(据说章太炎作文不用唐代之后的文字),思想太朦胧,不能让人一看便知。
阅读章太炎,仿佛在寒冬雪夜中望见一堆篝火,看似触手可及,只恨无路可走;它只是在召唤我们,指引我们,却无法温暖我们。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常常把人们按其是否喜爱章太炎而分成两类,从当时的舆论来看,那些不喜欢章太炎的人绝对不属于公正一类。
通过优雅细腻的笔触,四海为家的生涯,章太炎成为那个日益消沉的中华文化的讴歌者与代言人。至少在他的作品里,那个逝去的诗的国度又失而复得,这些作品回应了中国所经历的重重考验。在漫长的岁月里,章太炎的祖国成为军人体制的囚徒,而他的经历与作品则始终坚守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尤其是从正面引导着革命的创造力。更准确地说,他是包容甚至超越了革命的全部创造力的革命家。
解谜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纯粹、最诱人的行为。章太炎的身份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他不只是革命家,更是革命家的塑造者。他的目标是让他们免于成为那个时代的平庸产物甚至牺牲品。他总是以俯视的眼光把他们看作一队莫名所以、蠢蠢欲动的行列。
章太炎喜欢为革命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我们只知道这个谜底与慈悲有关。革命思想已被诸多支点与体系污染,而章太炎是向来不相信精神界有所谓杠杆或支点的。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与那些落难王公的酸气相比,他是文气逼人,贵气逼人。
在汉语中,革命是一种学问。章太炎古文功夫了得,被称为 “有学问的革命家”,一直是民国史书中的风流人物。作为一个研习宪法史的教书匠,阅读章太炎只能算作是业余爱好。不过,时间久了,便也在心中生出了种种问题疑惑,乃至执念:
章太炎人如其名,有一双火眼,游侠气质的火眼,这双火眼是如何观望中国法律的变革的?
章太炎是谜一般的革命家,学问好,又有佛学的底子,每以道家文体,写出佛家慈悲,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格?
章太炎迷恋旧时文化,仿佛一个落难的富家公子,隔着窗棂望见别人在自家旧宅宴乐,总怀着深刻的尊严感。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知识人阶层常有的尊严感?
章太炎投身革命,却时常活在一些浪漫的概念中,每每故作不同,人称 “章疯子”。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有时间,有精力,有自由,却舍不得拼命,舍不得疯狂,是不是有必要琢磨一下他的疯魔?
太炎先生不停地追问:一个年青的中国以何种姿态与那个年老的中国交谈?我的问题是,该如何安放这座灯塔,换言之,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想象章太炎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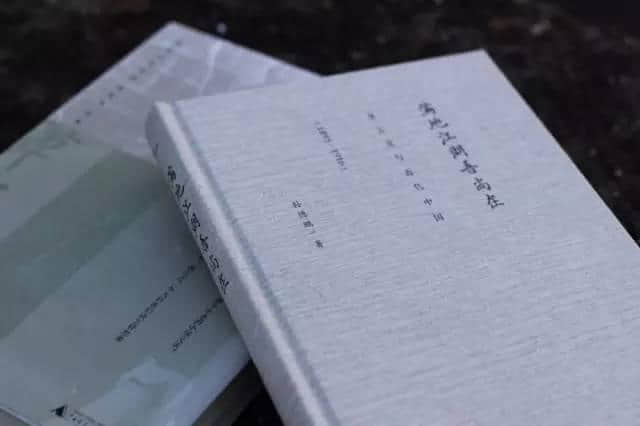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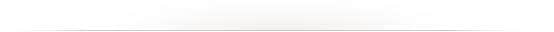
-END-
编辑丨廖茹画(实习)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1285次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