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崇效寺《青松红杏图》,说到张中行先生
李茂林

崇效寺
崇效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7),昔为唐代刘济舍宅所建,元代和明代都有大规模的修葺。明天顺年间(1457—1464)重修,明嘉靖时(1522—1566)于寺中增建藏经阁。清初,崇效寺有大片枣树,每至晚春,枣花盛开吸引诸多文人。清初诗人王士祯(王渔洋)称崇效寺为枣花寺。
后来枣花寺又以丁香和牡丹出名,也吸引不少文人墨客。除了诸多的应时之花外,崇效寺还藏有一名画——《青松红杏图》,据《燕都丛考》等史书记载,《青松红杏图》画卷,为明末清初扬州人的智朴和尚所绘,智扑和尚俗姓张,乃明末年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偏将,曾随洪承畴督师迎战清军于关外的松山、杏山。洪承畴兵败被俘,变节降清,而他偏不愿随洪承畴变节投降,遁入京东盘山寺出家为僧,取名智朴。他经历了松山、杏山之役,亲眼看到明军将士惨死疆场,悲愤之余,逐创作出了一幅影射松、杏二山战役的《青松红杏图》。据《燕都丛考》一书记载,图中“一老僧凭松而立,苍枝蚪亘,红杏夹之,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
此画卷被清初王士祯看到亲笔题写了“青松红杏图”五个大字,又在卷下题写了诗句。当时朱竹垞、王昊庐、查他山、陈香泉、孙松坪俱有题句。此后,凡文人墨客到崇效寺,都要瞻仰一下这幅珍贵的《青松红杏图》,并且在上面题咏。续题的人前后以千人计,其卷分为正副两卷,粗如牛腰。题写者中,历代名人有纪晓岚、洪亮吉、林则徐、李慈铭、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曾国藩直到鲁迅。人称“大观”,堪称京华之最!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张中行来参观崇效寺,回去以后,细细地写了一段文字,记载当时欣赏《青松红杏图》的情景,且看他在《崇效寺》一文中是怎么记述的:
“记得是秋天,观赏牡丹的人早已绝迹,寺里很清静,时间是上午,寺里还准备了午斋。我这次去有目的,是看《青松红杏图》卷。寺里招待的人很慷慨地拿出来,很粗的一个卷子,可见题咏之多。图画得平平。和尚画青松,取其坚而不惑,意思明朗。兼画红杏,何所取义呢?也许是以形象表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总之,这是因怪而奇。展看题咏,由清初到清末,有名的文人墨客包容不少,当作历史的遗迹,说是可珍重也不无理由。”(见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页212)
张中行先生说:“和尚画青松,取其坚而不惑,意思明朗。”却又说:“兼画红杏,何所取义呢?”于是他认为此画是“因怪而奇”。张中行先生写此文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他记叙的是年青时访崇效寺之事,难道六七十年间他仍然抱此疑问?作为北京文人,不知《青松红杏图》含义所在,实在有点OUT了。难道张中行先生真的不晓得画中红杏之意义?还是另有疑问与高见?吾不得而知。由此,我倒怀疑起张中行先生是新派人物了,因为传统文人不至于斯,五四后中国的假洋鬼子不明就里是毫不足怪的。至今《宣武区志》关于崇效寺记述中就根本没有没有言及《青松红杏图》,清代具有官方意味的《日下旧闻考》在绍介崇效寺时提到那里“枣树千株”,“万缘碑”“俶诡”,也没提到寺内藏有的《青松红杏图》。此《青松红杏图》抑或只是满清以后,大汉传统文人之情结吧。
又读到张中行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满井》——即袁宏道《满井游记》所言之北京安定门外之满井。张中行先生说:“是个有砌石围着的方形小池塘,即所谓‘井’,其中有水,即所谓‘满’。” (见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页233)老先生真有两下子,本来北京人所说之“满井”是指水溢而不喷涌之泉,是一专名词,张中行先生却要将“满井”二字分别具体落实,能不贻笑方家乎?本人觉得张中行先生作为“洋派学者”,倒也担得,视为传统文人雅士,无乃贬低乎?贬低何在?在于责人“学于洋”而不得,老而“归于土”也。

张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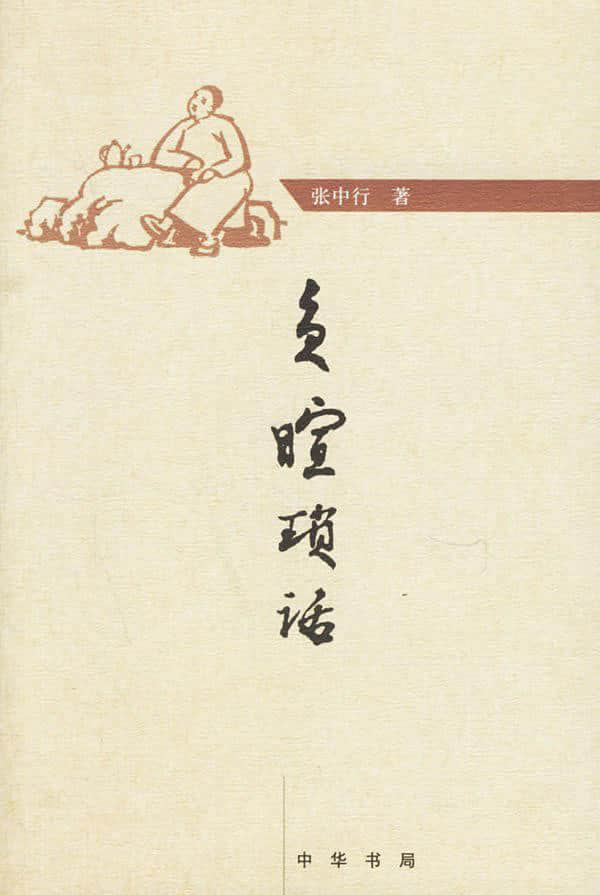
- 上一篇:关山万里雪
- 下一篇:战国策011·东周·周文君免士工师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