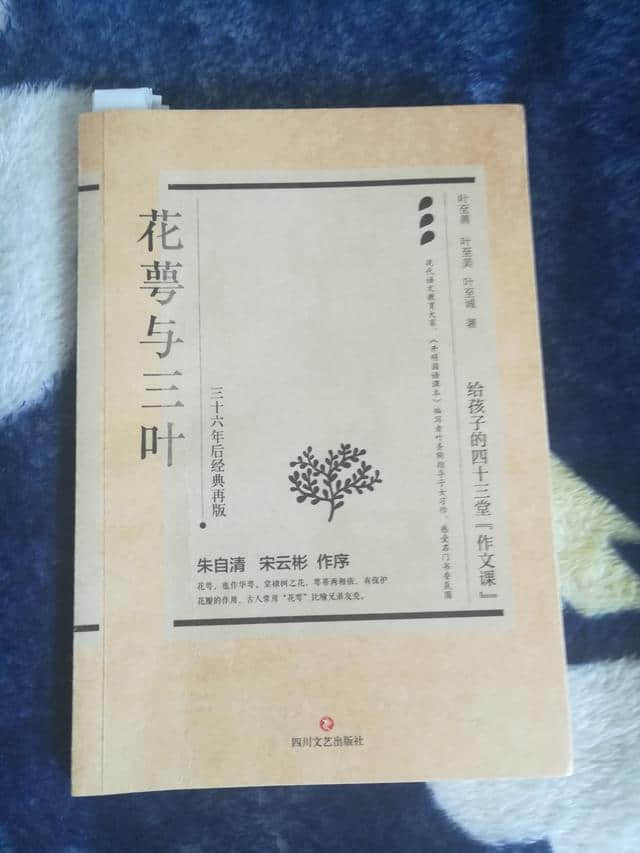
芝兰玉树,出自《世说新语》,被用来形容有出息的子侄辈。身为叶圣陶先生的子女,文笔不凡的叶家三兄妹,自然也是大家眼中,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在看到他们三人的文风都清新可喜、言之有物后,自然是连朱自清先生等人,也要在赞三兄妹文字功力之余,还要感叹叶圣陶先生和夫人“教子有方”,“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所以,毫无疑问,虽然三兄妹自谦道,两本集子都不过是“作文本儿”的水平,但其健全博爱的心灵造就的好文章中,处处展现出的观察的细致、思考的深度和不经意间就展现出的简明流畅的笔力,则的确远远超出其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甚至在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引起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的现代人的共鸣。
而三兄妹的文风与他们各自的经历或是性格,都称得上“很有辨识度”,的确是那种“不用署名就能分得清”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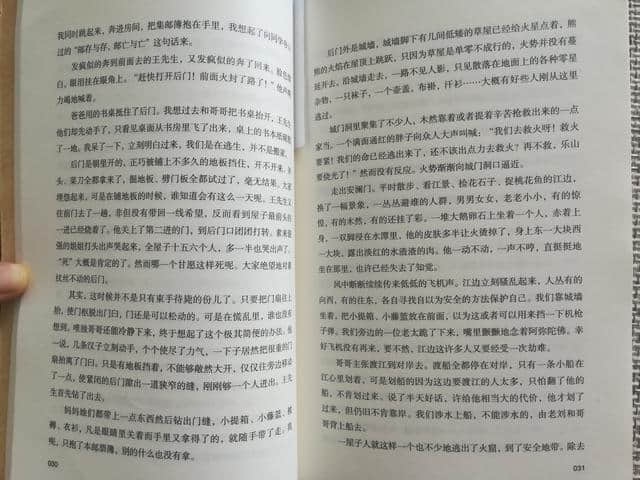
大哥叶至善,小小年纪就有那个年代要求他具有的“长兄如父”的心态,遇到大事也更显沉着冷静,能在家人躲避战祸、被大轰炸都吓得心胆俱裂的恐怖时刻,比一干大人还能先一步稳定情绪,帮大家找到了免被火灾困死的逃生之路,所以,选取的他的文章,似乎更倾向于中国古代文人要在文章中找到精神上的“清净”,或“暂时从尘世间解脱”的冲淡宁和。即使感物伤怀,为一副精美的画卷和一副对联的存亡而感慨,也只是在字句间淡然点出家人的狼狈处境,并不流于一味地伤春悲秋,却仍能引人联想起战争遗患的惨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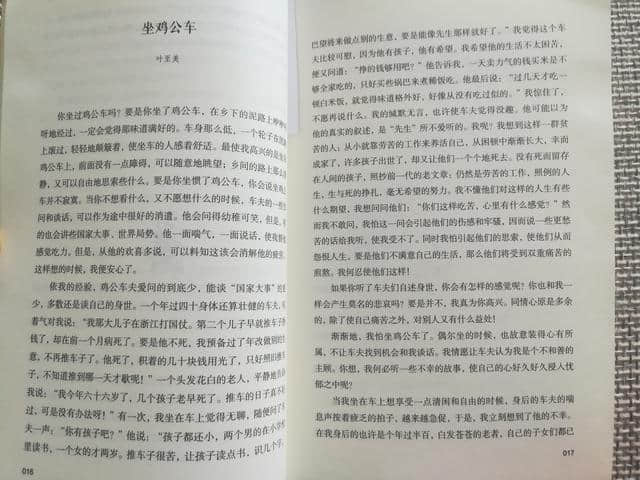
女儿叶至美,观察的视角中则更多一分女孩子独有的细腻,联想起社会问题的角度,也常常是兄弟们所不及的--比如,她坐鸡公车,会因为车夫们的不幸身世而联想到,到底是让他们倾诉出自己的痛苦才能让他们感到未来的日子还有奔头,还是让他们“习惯于痛苦”才是更恰当的呢?她在不同的中学,因为校规对男女生接触的态度和条例上的大不同,产生的对“自由”和“对自由之可贵的忘记”,不也很值得现代人好好思索一番吗?她的小说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佣工的去留和未来,如果是两个年轻人不能触及的沉重话题,那么,之前感受到的对方的情谊,又怎能一旦忘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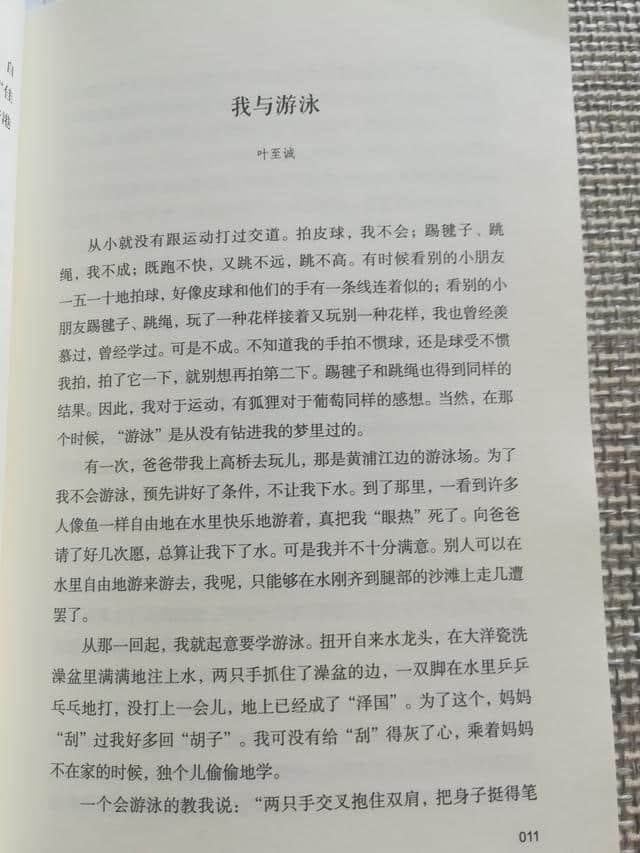
次子叶至诚,在书中的习作,就已经展现出了对文字的出色“编辑才能”,写出的文字,长短详略都十分得益,用词也从不刻意引用卖弄,即使是集邮、学游泳等小事,因为处处体现一腔真诚与热情,也每每让他的文字里自带一种平实却活泼的生命力,读起来也觉得生动--这算不算是叶家那种不干预各自的天性、言传身教却不刻意立规矩的氛围下,自然的产物呢?
我们每每感叹现在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快,却“缺乏感情”;我们诧异于现代孩子的早熟,却对诸多生活的细节一无所知;我们感伤于离自然越来越远,却以生存为借口,主动选择带着家人逃离乡野······但是,无论孩子们以后将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环境,父母都是“爱的园圃”,父母的言传身教都会是品质最美好、最珍贵的“苗木”们最初的依恋,而一旦它们成长到超过了能被“修剪”的范畴,长成“花萼”,还是“叶”,又有几分紧要?芝兰玉树的根,不是永远都在“园圃”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