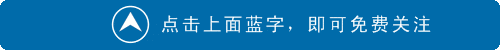

中国儒家典籍《论语》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法国汉学在世界汉学界地位颇高,成果丰厚,对《论语》的译介和研究历史悠久。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关于儒家学说对法国文化影响的研究,但截至目前,少有人以儒家典籍的译介为线索,来探讨儒家思想在法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文章梳理了《论语》在法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状况,展现了儒家文化与法国文化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的接触、交流和碰撞,进而分析各时期不同境遇的原因。

《文心雕龙·原道》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是说论文说道要向圣人学习。《论语》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记录了“圣人”孔子和他周围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和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影响和决定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从最初开始关注中国文化的那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到今天作为法国东方战略智库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国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中心从未偏离过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文化。
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关于儒家学说对法国文化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或重在海外汉学史整理,探讨不同时期法国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研究状况、法国汉学家研究成果等;或关注翻译中对语言层面的研究,比较不同译本。笔者搜集、整理并归纳分析了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期刊论文和极少数学位论文),发现以儒家典籍为线索,探讨儒家典籍在法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的研究并不多。同时,先前的研究者由于法语语言水平所限,可能在研究中并未使用第一手原文文献,导致有少数论文出现明显的信息错误,甚至有未经严密考证就随意引用不实信息,以至于以讹传讹的现象。本文将梳理《论语》在法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之境遇,展现儒家文化与法国文化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的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进而分析各时期不同境遇的原因。
一、 法译本的“前身”:早期欧洲的拉丁文译本
法国对《论语》的最初认识,与中法思想交流史起源于同一时代。中国与法国的思想交流,包括文学、文化、宗教、艺术等,最初是从17世纪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的。17至18世纪有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是传播中国思想的垦荒者,他们的贡献之一就是翻译中国经典。
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是第一批抵达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1579年罗明坚抵达澳门并逗留了八年多,期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礼仪。回欧洲后,他将儒家典籍《四书》全文译成拉丁文,翻译作品手稿至今仍然存放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有研究显示,罗明坚的翻译著作随后被发表,成为第一次在欧洲发表的汉学译著,遗憾的是当时欧洲主流社会并未对中国有太多的关注。
利玛窦到达中国后观察到,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培养始于《四书》,于是他也尝试将中国典籍翻译成拉丁文,随后又有至少17个耶稣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虽然这部译著并未出版而且已经散失,但是他的这一翻译行为是可以考证的。利玛窦曾在通信中多次明确提到他翻译过《四书》,并将译稿寄回了欧洲。在1594年11月15日的信中,他提到:“几年前(按为1591年)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能的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甫,届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1]143 有学者认为,利玛窦的译著在当时的中国长期被作为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课本,并成为后来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lippeCouplet)等人所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底本。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化典籍、礼仪习俗的学习、研究和翻译,可以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源头,并直接影响了后来持续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也可以认为,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行为本身就属于“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这一批到达中国时间最早的传教士来自意大利,加之礼仪之争时间持续时间较长,故笔者在下文中将上述内容及他们的拉丁文译本单独评述。
二、“礼仪之争”时期的另类布道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大冲撞的一次重要事件。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将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震荡。来华传教士们就种种中国礼仪———如祭天祭祖等是否是迷信或偶像崇拜、能否与基督教教义并行不悖、中国人对孔夫子的崇拜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洲人就中国礼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极大地动摇了欧洲封建神权的绝对权威,罗马教廷为息事宁人费尽周折,焦头烂额之下最终宣判中国礼仪属于迷信,禁止通融。

传教士在这场争论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介绍,这一时期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对孔子思想的介绍颇多。“在所有的传教士中,入华耶稣会士可能是最有学问者。所以,唯有他们才理解绝不能正面与崇拜孔子的古老礼仪相对抗,因为孔子‘奠定了天朝帝国的社会制度形态,从而也确定了其行政制度’。”[2]75 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合作翻译了《论语》拉丁文版本。1687年,巴黎出版了由柏应理、殷铎泽、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和鲁日满(Franciscus Rougemont)共同编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书中附有《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这些译文就是以郭氏和殷氏的《论语》、《大学》译本为基础的。由于当时正值“礼仪之争”的高峰时期,拉丁语又是当时的“学术语言”,这个作为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一出版就反响强烈。该书在欧洲学界刮起了一阵中国思想文化之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地位颇为重要。
“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对儒家典籍翻译的掣肘之处在于,它使这些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工作饱受争议。随着传教士内部的论战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认为中国典籍翻译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悖,这使得教会中的本土主义者占了上风。在他们看来,耶稣会会士们即使已经开始放弃他们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结果也徒劳无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因素的影响,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虽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并没有很快被译成其它欧洲语言,因此也未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可以算作《论语》和儒家著作译文的还有1688年法国人西蒙·富歇(SimonFoucher)出版的用法文撰写的《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Lettres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和让·德拉布吕纳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Chine),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此书是法国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但是,尽管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比较草率。同时,这两本著作并不是对孔子论著的翻译文本,而只是对先前出版的拉丁文译本的概括阐述。而且在这些概括性的介绍中,《论语》只是被翻译为几十条毫无趣味和文学美感的伦理说教“箴言”。书中并没有明确表现出孔子及其作品的具体内容和真实价值,因此很难使读者对此书有更深入的了解。
1687年12月,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刊登了一篇对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评,作者是法国新教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Clerc)。书评后附有由他本人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16段《论语》译文。书评长达68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在其中显示出对《论语》的浓厚研究兴趣,认为孔子的思想广泛而丰富。他对之前耶稣会会士们的编撰著作中的某些信息持保留态度,认为他们模糊了孔子自己的论述以及孔子作品中某些段落出现的评注等。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1711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 ois Noël)的《中国典籍六种》,其中也收有《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此书后来被转译成法文,于1784年至1786年间在巴黎出版。由上文可知,中国典籍作品传播至欧洲时,大都是先被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被转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等欧洲国家各自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规律性线索。
三、18至19世纪法国的“汉学热”:对《论语》及儒家思想的推崇
法国一直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这归功于早期法国传教士和法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介绍、研究中国典籍方面的重要贡献。从1776年起,法国开始编辑出版在华法国传教士的汉学论文集《中国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之研究》(十六巨册)、《海外传教士耶稣会士通信录》(十六卷)、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Moyriac de Mailla)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巨册),这把法国汉学推到了一个独霸世界汉学研究之圣坛的地位。[3]59⁃60 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书,该书46卷,是18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当时正处于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试图以哲学、理性的权威来代替基督教神权的权威。而经过耶稣会士翻译到欧洲大陆的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反宗教论者提供了攻击宗教文化的极好武器。他们对非宗教的孔子学说的理性客观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崇拜。但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家对《论语》及儒家典籍的了解主要是依托前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译本,启蒙思想家们以此为中介,研究了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
对于孔子以德服人的气魄,伏尔泰表示十分赞赏;伏尔泰也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一种政治体制。作为“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推崇孔子及其学说。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有些行为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在西方民众心目中,“救世主”耶稣的崇高地位是不言而喻、不可侵犯的,可是伏尔泰竟然敢将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并且早晚礼拜,二十年如一日。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该成为众人牢记的座右铭。自此之后,无数启蒙思想家都对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阅读相关的中国典籍翻译,而且还常常对典籍中的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了许多经验、教训。法籍德裔的霍尔巴赫(Heinrich Diefrich),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无神论者。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且他又提出“德治”主张,向大家号召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Denis Diderot)编撰了《百科全书字典》,在其中他赞叹说,孔子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而且,他也在其所编撰的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Chine)”和“中国哲学(Philosophie des Chinois)”两个词条。此外,作为三权分立思想的提出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赞美过中国的德治思想,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4]122
纵观启蒙运动时期,尽管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儒家典籍《四书》是由传教士完成的译本,但是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译作曾经在法国,甚至在欧洲掀起过一股中国热潮,无数思想家因此为之倾倒,为之迷狂。儒家学说中的“仁”、“德”等核心概念更被广泛提及和运用到法国和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曾把《论语》里面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Ne fait pas à autrui ce que tune voudrais pas qu'on te fasse),作为自由道德标志而写入他自己所起草的《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et du Citoyen)。[4]122
此外,18世纪重要的孔子研究著作还包括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于1785年出版的《孔子传》。钱德明被认为是入华耶稣会士中的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有关中国的著作很多,能用汉语、法语、满文、蒙文著书立说,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启蒙运动的浪潮过后,19世纪法语翻译史上产生了几个重要的《论语》译本。汉学家波蒂埃(Guillaume Pauthier)于1846年出版了《四书:中国道德和政治哲学》(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6)。书中全译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并在导论和序言中做了相关评述,给予孔子极高的赞誉。波蒂埃译本的价值还体现在,与先前由拉丁文译本转译成的法译本不同,它是第一部根据汉语文本直接翻译而来的法译本。除此译著外,波蒂埃还有多部汉学著作,研究涉及中国历史、文学、文化,代表作有《现代中国:中华大帝国之历史、地理、文学述写》(Chine Moder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Géographique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于1895年在巴黎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法译本(Les quatre livres:La GrandeEtude,L'Invariable Milieu,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de ses disciples, Oeuvres de Meng Tzeu (SeuChou))。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编写过辞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他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用法文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为卓著者之一。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评价说:“顾赛芬的法文、拉丁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他的翻译严格忠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没有做任何独出心裁的解释或个人评论的意图”,“顾赛芬的译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5]他的译本被多次再版,是《论语》众多法译本中最经典的译本之一。他翻译的儒家典籍除《四书》外还包括1896年出版的《诗经》、1897年出版的《书经》和1899年出版的《礼记》等。
四、20世纪以来《论语》法译的研究转向
如果说早期法国对《论语》的研究是以基督教神学研究附会孔子的儒家学说,启蒙时期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自身革命寻求武器的话,那么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有了新的转向。这个时期的学者最大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等信仰的苑囿,以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方法论,来研究《论语》和儒家思想。“一般来说,法国现在的倾向是更新传统性的汉学,甚至是断然地从中摆脱出来,一直超越传统的分界,并将从人文科学借鉴来的方法论(结构论、符号学、认识论等)纳入其中。”[6]97
这一时期,法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学研究机构和大学,其中较为著名的儒学研究机构有: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 aised’Extrême⁃Orient)、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 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4]123 。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起设置汉学教授讲席,这标志着法国汉学研究从宗教化开始转向世俗化。法国多位著名汉学家都对《论语》的译介起过积极作用,有着卓越贡献。
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其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人思维》(LaPensée chinoise)中,专列一章介绍孔子和他的人文主义精神。葛兰言多处引用《论语》的章节并做了翻译,特别是对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文化负载词,如“君子”、“小人”等的翻译方式,做了专门探讨。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是另一位直接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教学工作在过去的数年里一直集中在介绍中华帝国早期的儒学作家”,“在他的心目中,儒学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特征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7]113
师从汪德迈教授的程艾兰(Anne Cheng)是法籍华裔知名学者,多年来也一直从事法国的儒学研究。她于1981年在法国Le Seuil出版社出版了《<论语>翻译及简介、笔记、地图和年表》(Traduction intégrale d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avec introduction,notes,carteset chronologie);1985年,此书在同一出版社再版;1992年,又由该社收录在《人类的伟大经书》(Les grands texts sacrésdel’humanité)丛书中再次出版,她的译本一直是权威的法语译本。除翻译《论语》外,程艾兰的儒学研究著作《汉代儒学研究》(Étude sur le confu⁃cianisme Han,1985)和《中国思想史》(Histoire dela pensée chinoise)均获得极高的赞誉。特别是后者,在法国和整个西方汉学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比利时汉学家皮埃尔·里克曼于1987年出版了《论语》的法译本,由东方知识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亚国籍的他以西蒙·利斯(Simon Leys)的笔名于1997年出版了《论语》的英译本。由于作者本人也是小说家,他在《论语》引言中谈到,他并非将《论语》当做思想巨著,而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他为他的译文预先设定的读者是普通人,而非学者。他的英语译本中注释旁征博引,涵盖大量西方文化,便于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相比之下,法译本中的注释偏少。
另外一个法语译本是由法国汉学家雷威安(André Lévy)翻译完成的。雷威安是法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童年时期在中国度过,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情结。他的译本《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录》(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disciples)于1994年在法国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雷威安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做了很大贡献,除《论语》外,他的著作主要还有《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白话小说》、《中国古典文学概览》、《金瓶梅词话》、《西游记》、《聊斋志异》、《牡丹亭》等,这些译著被西方读者广泛阅读,在法国汉学界很有影响。
当代围绕《论语》的译介以及对儒家思想进行的研究,除上述翻译成果外,还体现在汉学家的研究中,包括当前在法国汉学界、比较文学界都引起极大反响的著名学者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 ois Jullien)、马克(Marc Kalinowski)等。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马蒂厄(Rémy Mathieu)2006年出版了《孔子》一书,书中的翻译涉及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多部儒家典籍,并集中了包括四书五经、《孝经》、《荀子》等经典文献在内的主体性阐述。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王论跃教授在《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8]25⁃32一文中有全面的介绍。
五、结语
通过整理法国对《论语》的翻译和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法国不同时期对这部典籍及其承载的思想的接受状况受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受当时法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法国社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影响《论语》在法国的接受状况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笔者以这个标准,将本文的结构划分为早期拉丁文译本时期、礼仪之争时代、启蒙时期、近代和现当代。其次,受译者和研究者身份的影响。从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理论、比较文学接受学理论、阐释学理论等角度,都可以论证这一因素的影响。译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包括其教育背景、生活经历、职业等,都决定了他将以何种眼光、出于何种目的来阅读《论语》、用何种方法来翻译、研究《论语》。在上文中提到的译者和研究者中,有初次探索神秘东方的欧洲传教士,有想从东方智慧中寻求武器的启蒙思想家,有对中国文学文化有浓烈兴趣的汉学家,有单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当代思想家,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各自对《论语》的接受状况。
在当今法国学界,如何解读《论语》,如何研究儒学和中国思想,依旧存在不同声音之间的激烈争论。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论语》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但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源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文本,对它的研究在任何时代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利玛窦书信集[M].罗渔,译.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2][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例[J].2010(3):57⁃62.
[4]谢欣吟,成蕾.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J].华西语文学刊,2012(2):120⁃123.
[5][法]保罗·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中[J].秦时月,译.中国文化研究,1994(1).
[6][法]汪德迈,程艾兰.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J].世界汉学,1998(1):97.
[7][法]程艾兰.儒学在法国———历史的探讨,当前的评价和未来的展望[J].孔子研究,1989(1):113.
[8]王论跃.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25⁃32.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