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是二程理学的基底,不论是性善、王霸论,或是内圣外王之系统,皆自孟子思想中发挥,可说是二程思想的重要来源。二程不仅信服孟子,并以继承、传受圣人之道为职责,在程颐所写〈明道先生行状〉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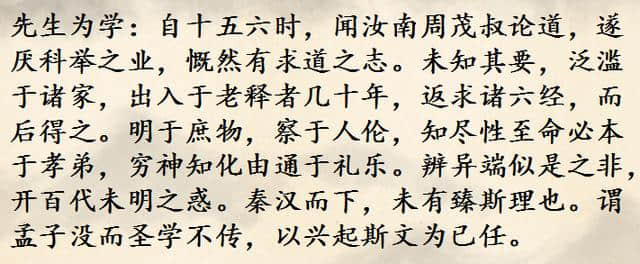
虽然这是程颐对程颢的描述,但也可看作是程氏兄弟的写照,二人承接了在孟子后断绝一千多年的儒学空白,并以振兴道统为己任。且因王安石新政的原故,二程更加致力于发掘儒家本身原有的内圣之学,好取代王氏新学。

亚圣孟子像
二程将“道”称作理,“理”是二程思想之核心,以“理”将宇宙观、道德观、人性论等议题串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宇宙观来说,万事万物皆自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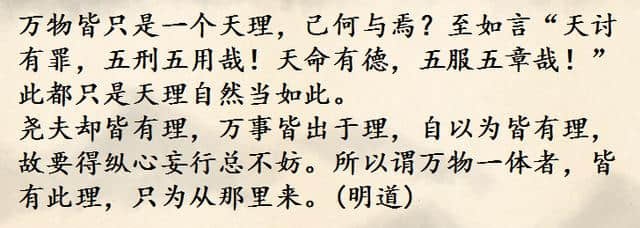
此理是呈现一种自然的状态,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事物依规律运作,但不会影响到理的本质,也不会改变理的状态。所以人类社会的更替变动,并不会使理有所生灭、增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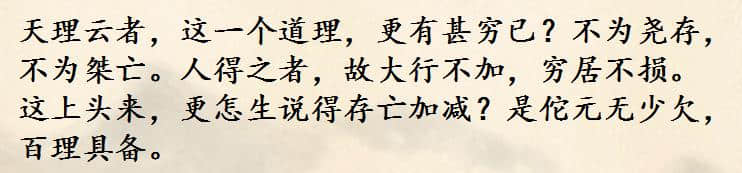
到这边天理的本质已出来,是永恒与超越的,并贯通万事万物中。但既为一个最高范畴的标准,自然不具意志,人为也无法撼动,那么天道与性命要如何连结?即宇宙与人性的关系为何?

二程文化园
这是王安石、周濂溪、张载都未完成的课题,而二程思想的价值所在便是解决了这项议题。从万事万物皆自理来,人也不例外是从理而生;理赋予事物自然之性,人性亦是从理来。于是开出“性即理”的说法,程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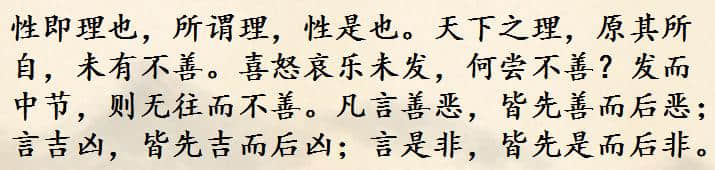
理既是超越、普遍的存在,其性质是纯然至善的,因此它赋予在人性中所展现的性是纯善之性。二程将此性称之为“天命之性”、“义理之性”,并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即是此性,程颐说:
二程将孟子和告子的性区分开来,认为两人所谈论的性都是人性,但层次不同。告子所言为“生之谓性”,二程称作“气禀之性”、“气质之性”。因为气有清浊,所以此性有善有恶。程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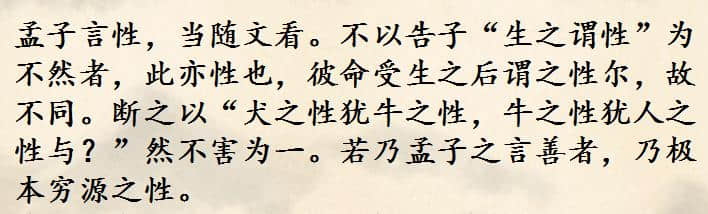
因此人具有两种性,一为天命之性,此性是人与天理的连结;一为生之谓性,此性解释了人的善恶行为。二程的人性二元论,将孟子所言善性视为前者,不仅肯定孟子性善论,还将层次拉高为“极本穷源之性”,是自天道、天理而来,是天所赋予的,也肯定了人性为善。二程认为这是孟子论人性不同于荀子、告子等人的高度。孟子所言是人的道德性根据,荀子性恶、告子生之谓性是事物的生物性。

二程夫子林
到这边,二程将人之所以为人的论证完成,从宇宙生成天理孕育万物,并赋予人性故有的道德善性,这个道德性是人与万物之生物性的重要区分,是天道性命的连结。但这里只解释了天道到性命的路径,如此还不够完整,因为这仅只于建立出一个儒家自身的宇宙观,尚未解决的还有人在这宇宙要如何自处的问题。即建立一个儒家自己安身立命的人生观,再进一步说明就是从性命回到天道的这条路径。

大美伊川二程文化园 内部
因为天道性命相贯通,不应只是天道下贯到性命,性命也应上通至天道,如此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天道下贯到性命的部分,已知是宇宙与人之间的关联,而性命上通至天道,则是说明人的生命范围里,要纳入整个宇宙、自然界,才得以有一个大格局的生命观。那这条从性命回到天道的路径要如何开启,二程认为要从“心”去识得。以“性即理”的观念来说,人的纯善之性是与天理的连结,只要能够透彻地了解此性,便可与天理相连,然要将性认识得透彻则要根据心,二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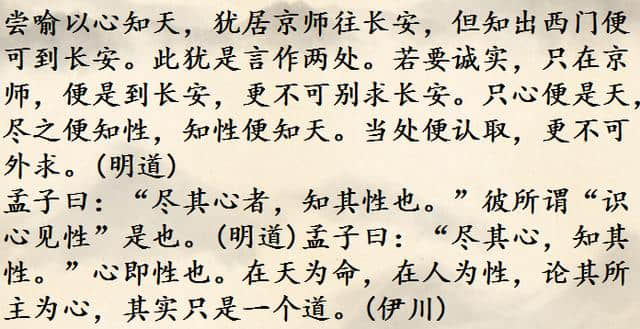
此修心尽性知天便是从性命回到天道的路径,这个观念是从孟子来的。但人性除了纯善的“义理之性”外,还具有“气禀之性”的清浊影响善恶。因此人心会受到浊气所蒙蔽,会受到私欲、外物等阻碍影响认识天理。程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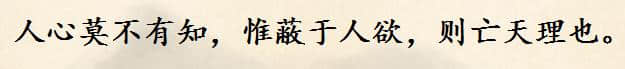
人心存有能知天理的条件,但要能不受到人欲影响,就必须下工夫来知心,以达知性知天的境界。然二程提出的工夫论不完全相同。程颢认为心是与道德同源,皆自理出,应从熟悉自身的道德开始来察觉仁心。程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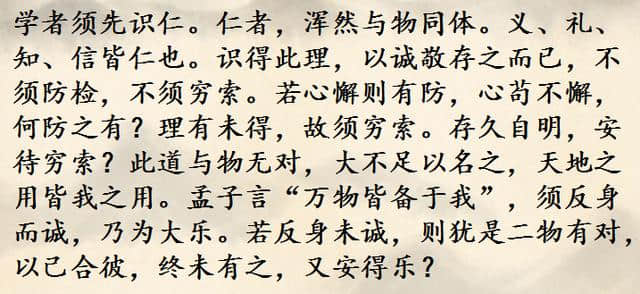
人心中存在固有的道德,仁的至高境界是与万物同为一体。因此藉由内向的自我体验道德,审视自身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即“反身而诚”,便可达到与物同的天人合一境界。因此从心中固有之道德去体证,即当从内证不须外求,以至于道。至于外物的影响,可以从张载提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问题,见程颢的回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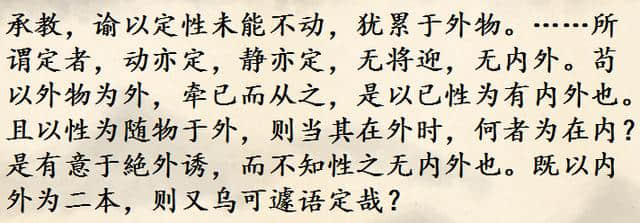
若能了解物与我相通的境界,便不会有内外分别,如此不论人、我、事、物是动是静,只要顺应事物的来去,而非从自我的利害出发去划分区别,便可除去个人因利害所产生出的负面心境。即正确地、适当地处事应物,不以自己的私心去待物。然后能定性,达到心境上的自由与安宁。

程林
不同于程颢的工夫论,程颐则是认为在修养内在精神的同时,也不应偏废知识的累积,藉由对外物的认识来达到充实自身的理性自觉。因此程颐有“格物穷理”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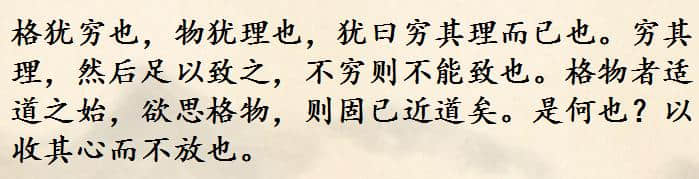
道德修养应是内外兼并,不应偏颇一方。但为何要格物?程颐认为事物和人一样皆自理出,且各自有理,即一物皆有一理,经由格物的累积可达同一理。因事物有千千万万种,所以格物穷理的方式有许多条路径可以走,而最终都将导向一个道理而已。程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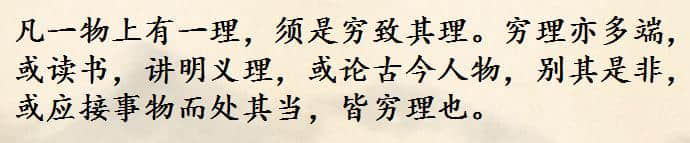
不论是读书、明义理,或是论古今、人物是非,或是适当地皆应万物,这都是求道的路径之一。求道的方法之多,意在不要只专注于一事或一物,生命格局要放大去包容整个宇宙自然,更要从千万事物中去观察体验。要注意的是“格物”最主要目的是格身心,而不是拘泥于眼前的事物。人在修养自身内心的同时,也应认识知识使之不断累积,然后从经验中反省、学习,进而能够实践道德,让自身内心趋近于圆满的状态。
尽管二程两人的工夫论不尽相同,但皆是强调实践道德、心存道德,即从自身固有的道德去发挥,因为道德即是天理,因此发挥道德性,便是遵循天理的规则运行。道德在人类社会的展现是伦理纲常,如君臣父子之义,忠孝信义等,所以生为人在社会中要实践道德以达天理,便是遵循伦理纲常的指示去行动,君尽君道,臣尽臣道,便是遵循天理的运作。如此便间接以天理之说巩固了宋代朝政的稳定性。就二程的理学系统对皇权的影响,姚瀛艇先生就认为:

程庙
根据神学目的论,“皇权”是天之所命,伦理纲常是神意的体现,服从伦理纲常,是被动地服从“天命”或“神意”。根据理本论,“皇权”是天理的化身,伦理刚常是天理的体现,服从伦理刚常不仅是服从“天理”,而且是自我人格的完美体现。神学目的论还隐藏着对“皇权”不利的因素。企图改朝换代的野心家,可以借口“天命在我”,从而据此去篡夺政权。于是,皇权便不得不陷于既提倡“天命”,又严禁别人“妖言利害”的矛盾之中。

二程画像
理本论却没有这样的危险性。因为皇权就是天理的化身,服从天理就必须服从皇权,服从皇权亦即服从天理。对任何王朝来说,不存在“天理可改”的问题。这就杜绝了任何野心家的借口,皇权再也不必去干既提倡“天命”又严禁别人“妖言利害”那样自相矛盾的事了。总之,洛学为皇权和伦理纲常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皇权和伦理纲常得到了完美的论证。这就是洛学终于成为官方哲学的关键所在。

程园二程墓
不过二程是反对绝对的皇权,因此在以天理巩固政权的同时又要不让皇权无限扩张,二程设下条件,运用孟子王霸论和君臣观来限制。而洛学成为官方学术则是在宋室南迁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依旧是王学的势力。
到这边可以看到从二程所建构的理学系统,将宋初以来思想家一直忽略的“内圣”部分给补足,亦将王安石首开的内圣与外王连结的观念,比其发挥的更加完善。二程将儒学以老店新开之样貌,添加了新的元素与内容,扩展了儒学的格局以及读书人的视野。
参考文献:
- 《孔子与论语》十、〈四书义理之展演〉
- 《河南程氏遗书》
- 《宋代文化史》第七章〈新儒学的形成与哲学思想的演变〉
- 《河南程氏文集》
- 《孟子注疏‧尽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