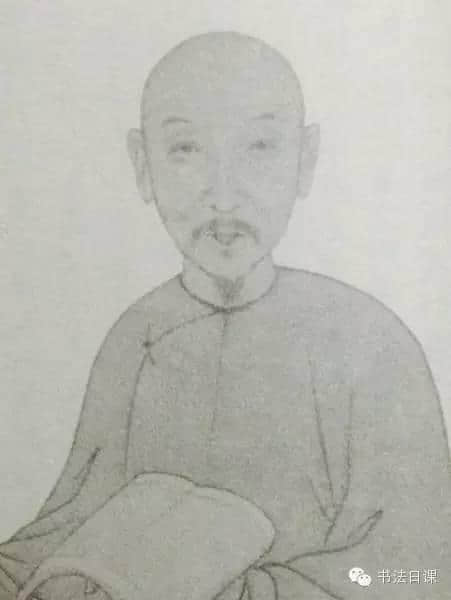
最近因撰写《明清政治思想史》,拜读了李锐先生发表于《读书》2009年第8期的大作《傅山们的羞耻心》,感到尚有未得我心之处。梗噎在喉,一吐为快。
易代鼎革之际,饱受忠君观念浸润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道德压力。诚如李锐先生所言:“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皇帝的尸体,对遗民们,尤其对那些以前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无疑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剧痛和煎熬……大变之际不能忠君殉国,活下来就是苟活,活着就是屈辱”,因此傅山才在自己的诗文中反复慨叹:“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倘若对傅山的理解在这里停下来,则他与历代那些在君国颠覆后苟全性命的遗民没什么区别,因而李锐先生特别强调傅山们“从拒绝出仕,转而为追求承担文化正统的代言人。在书法上的回到源头,让审美的品位追溯古人,师法前朝,就成为他们深邃的精神寄托”。在李锐先生看来,傅山等亡明遗民将劫后余生都用在了对道德原罪的自我救赎上:通过文化使命的担承、审美风尚的创新,使不能以身殉国的羞耻感得到纾解。
而在大多数学者笔下,傅山被描述为一只脚踏进“近代”的先觉者,是对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进行清算的“启蒙思想家”。如葛荣晋先生称傅山的“反常之论”具有“近代启蒙的特色”,“是城市市民争取政治权力意识的反映”;张立文先生认为“傅山作为启蒙思想家,是一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岑贤安强调傅山“站在新兴工商业市民阶层的立场上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主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侯文正《傅山传》把他定论为中国十七世纪启蒙思潮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尹协理在《奇人傅山》一文中说他“态度鲜明地成为农民与市民的思想代表”。
我认为,无论是李锐先生眼里以文化救亡自赎的遗民傅山,还是众多学者笔下那个以思想启蒙为志业的战士傅山,同样是单向度的。此类单向评价带有很大的想当然成分。它为傅山的人格形象打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辉光,使他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存在物,以至于在把他作为伟大历史名人供奉起来的同时,我们也远离了他所挣扎于其中的生活的感性,丧失了通向他那孤迥而绝望的内心世界的幽径。
走进傅山的世界,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通天彻地却又无可告诉的孤独感。那是人类历史中某些特殊境遇下才会产生的一种生存体验,是只属于不世出的天才傅山的孤独:其中既有一体万物的宗教家的孤旷、以空观有的哲人的虚寂、直面人性的诗人的悲悯,也有自我放逐的忧伤寂寞,还有勘破红尘的傲世佯狂。周国平先生说,唯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傅山的孤独是一种绝望的孤独,因为他没有上帝,没有神明,他所面对的只是无限和空虚:不惟山河变色、社稷飘零,用以安身立命并赖于慰藉其“羞耻心”的文教传统也变成了废墟,看不到自振生机的希望。在内心深处,他并非“萧然物外”的自畅天机者,他有着强烈的入世倾向和现实关怀。三十岁时,他曾约集全省诸生,赴京为受阉宦迫害的山西提学袁继咸上书请愿,在京师广散揭帖,带头号呼于官署,为一时风云人物;明室败亡后,他着黄冠入山,却时刻以某种方式关注和支持外面的抗清斗争,并一度为图恢复而奔走。奈何世道人心无可凭仗,日落烟沉后只好“物外萧然”。可以说,对社会,他是不得“入”才“出”;对世人,他因奏“雅”而弹“俗”(世俗之俗而非庸俗之俗。他认为“雅”已被奴儒所糟蹋,在“俗”中还有一点真性情)。寄身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他掉臂游行于稠人广众,亦龙亦蛇,时入时出,其内心的孤迥实非常人可知。把自己的文集题名为《霜红龛》,应是大有深意的:霜叶之红艳,非天日之明光,然亦非草木之原色;而“红”仅“一龛”,则非关时序之转替。显然,傅山要表达的是:固然不能改变世界,却能够坚守自己。他以自己的愿力所守护的这一方世外净土,实际上是追悼华夏故国的最后一个祭坛——他把自己奉做了献祭的牺牲。
与现实世界的疏异与支离相对应,傅山眼里的宇宙也变得恢弘而苍凉:再也没有至善的“天理”妥帖地安排万有,而只剩下无情的“运势”推动着事物移转。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再是圣王之道所构筑的秩序的坛场,而呈现出荒莽和“无理”的本相。在傅山看来,芸芸众生所具有的盲目的、整体性力量是人类历史之内在活力的体现,也是天道之自然的体现,看起来“无理”却最合乎自然之“理”;而统治者所进行的一切文化规训和制度建设,不过是为了维护现实统治进行的人为建构,看起来是“有理”的,却会随着时势的改变而丧失其合理性——沦入“无理”。在混沌的“无理”面前,“理”是脆弱的、暂时的,因而“小人多胜”,小人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根本性力量。这样,他通过颠覆“有理”与“无理”的关系,剥夺了专制权力的天然合法性。
天理不足恃,民族的伟大历史和文化传统遂成为傅山们最后据守的壁垒。同黄宗羲一样,傅山希望通过追溯、探讨民族的过去接文明之坠绪,传前圣之道统。因此,他对夷夏之大防耿耿于怀,对历代相仍的“正闰”之辨尤所措意。他曾告诫子孙细读《史记》、《汉书》,强调将金、辽、元三代之史视同载记,“不作正史读”。他还重视对明清鼎革之际史事的记载和资料的收集,并模仿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在所记史事后面加上“野史氏曰”、“闾史氏曰”之类的评语。这种为千载留正史的抱负,体现了他对自己所担承的文化使命的自觉。黄宗羲有名言:“国可灭,史不可灭”。其实这是他们共同的信念,也是支持他们在海枯石烂之后孤标自振的力量源泉。
对历史的守望本来就是孤独者的志业。傅山们的悲哀在于,辉煌只属于过去,横亘在眼前的只是一片废墟——文教传统的断壁残垣。更加悲哀的是,制造这废墟的不是清朝的铁骑,而是发自人心的颓废和腐败,是不可救药的世道的沉沦。傅山在人的社会性本然存在里发现的是“无理胜有理”的警诫,从原本凭为依托的文化传统里收获的只有灰心:孔子开创的内外合一的伟大学术沦落为墨守师法的章句训诂,或驰骋心志的狂禅臆说;六朝烟雨浸润的江南绮丽地再也培育不出价值创新的苗稼。因此,当顾炎武以瘦骡驮书、风尘仆仆地巡视北方大地的山河形胜、意在为后人解说天下进退之势、兴亡之由时,傅山把目光由文化中心江南收回到自己所生长于斯的家乡——僻处西北的山西。那是一片雄伟的高地:它以太行山为脊,横断东西,是京津及华北平原的强大屏障,也是中华文明抵御外来侵略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希望凛冽的西北风能够振作这个萎靡已久的民族的心气,强健这个衰颓已极的社会的筋骨。因此他在诗文中刻意营造一种“北方气象”,提出了“西北之文”的概念,指出其特点是“沉郁、不肤脆利口”,强调作文要摒弃靡丽滥艳、熟腐圆滑,追求一种简古生硬的奇崛之美。他自称是“西北之西北老人”,表达了远离尘嚣、独面旷野的决心。
也许傅山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对“西北风”的执着正透露了对民族伟大历史的迷恋与不舍:秦时明月汉时关,纵横大漠风沙的金戈铁马,激扬、熔铸了令后世千载神往的汉唐风骨,因而他把那里看作精神的故乡。然而,无情的现实是,世运已转向东南,来于海上的坚船利炮将在某一天把中华大地陷入更加激烈、惨痛的变局之中。这些傅山不可能预见到,他只是在极度失望之后凭诗人的敏感本能地退守到所应退守之处——傅山的直觉没有犯错,民族的根脉就埋藏在西北那一片历经沧桑的高山厚土里,三百年后共产党人正是据西北而定天下,揭开了华夏历史的新篇章。从热闹的中心抽身而退,向英雄继踵的荒天大野里追寻民族精神的一脉灵明,他注定了要经受孤独的煎熬。
对现实文化的失望引发了傅山对“奴俗”的痛恨。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都把明朝败亡的原因归于知识阶层的空谈误国,傅山则进一步,指出知识阶层人格的全面堕落导致的文化腐败是明朝倾覆的深层原因。他把这种人格堕落的表征概括为“奴性”,其主要症状为脊骨疲软、大脑僵化,心地暗昧。傅山对“奴俗”深恶痛绝,称“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在论及书法时,他最厌恶的是“奴态”、“婢贱野俗之气”、“奴俗气”,如《霜红龛集》卷二五《家训》有:“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对那些固守鄙陋、不辨是非的读书人,他斥之为“奴儒”、“奴师”、“瞎儒”,是扶不上墙的“死狗”。他认为“奴人”的广泛存在像深入腠理的慢性病一样侵蚀着社会的活力,明朝所以在短时间内一败涂地,是因为年深日久累积的“奴气”耗尽了它的生机。在《霜红龛集》卷九《五言律》之《读史》一诗中,他把“奴人”喻为天地之“腹疾”,渴望凭借神明之力除残去秽:“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这不禁使人联想到龚自珍的《己亥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天迥地旷,遍地奴俗;俯仰今古,目无余子:这种先觉者的孤独寂寥之感,可谓天荒地老无识!
因之,书法与绘画,这种个人性的技艺,成了傅山为自己和社会采取的治疗手段:对奴俗的疏泄与矫正。在《训子贴》中,傅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美学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在其书法名作《啬庐妙翰》中,傅山几乎以偏激的方式把这种主张推向极致:全卷由书体和书风各不相同的许多段落组成,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结字和章法杂乱无序,有时字与字堆砌在一起,且大小悬殊;有的字笔划彼此脱节,结构严重变形;为达到陌生和怪异的效果,傅山还大量使用俗子、异体字甚至自造字。总之是率意为之,有些段落常人看来如同天书。傅山的画追求的也是一种荒疏的效果:峰峦树木则稀奇古怪,家居人物则萧瑟凄凉,建构的不是隐士怡情适性的境界,而是遗民自我放逐的空间。
傅山以书画赢得风流名士的艳名,但他从来没有把书画当作值得全力以赴的事业。除了自我宣泄,有时候他借游戏笔墨游戏世界。当看到他率意而为的“大作”被附趋风雅的众人奉为至宝时,一定在内心里感到某种恶作剧般的快意,同时肯定也会产生一种“我谁与归”的悲凉之感。他曾这样近乎玩世般自我解嘲:“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就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凌娟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无用之才或为大才。傅山就像庄子笔下伫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的千年老树,独抱沧桑心情,只把纷纭世象当作过眼风景。
李锐先生的文章是对白谦慎先生所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的品读。在书的导言中,白先生指出:“在十七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认为正是充满异质的晚明文化,为艺术家的标新立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此,李锐先生附和道:
纸面上的笔走龙蛇,纯属书法家的个人风格和爱好选择,可是,当这种个人的选择演变成为对于什么叫美的重新定位时,当这种重新定位最终改变了几百年的审美观,最终成为人们谈论美、成为人们讲究品位的标准时,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所谓明朝、清朝的朝代之争,所谓改朝换代的山崩地裂,都因为时间而变得无足轻重,可人们对美的选择和品位却显得深沉而又悠长。
尽管也提到了政治情势和学术风气的影响,他们两位强调的都是艺术嬗变的内在逻辑,关注“这美是如何在历史的困境中步步为营地煎熬出来的”。他们把艺术看作对现实的救赎,看作从生活的苦难中绽放的精神之花。出于对傅山的尊崇,他们或许不愿承认,艺术是构成现实本身的要素,其形式有时候与“美”无关。晚明时期对古拙与怪奇的追逐,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审美趣味,还不如说是一种病象——因治病而导致的疾病,而傅山只是这时代症候群中突出的代表——病叶先知秋,最敏感的天才往往病得最重。
傅山以书画救治文化,以医术救治肉体。他在世时“擅医之名遍山右”,被誉为兼有神思与高韵的“仙医”。然而,面对作为救治对象的芸芸大众,他有时候同样感到一种深彻骨髓的寂寞,因为他的神思高韵少有人领会。他曾半是诙谐半是无奈地叹惋:
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以髙爽之医治奴人,奴人不许;以正经之医治胡人,胡人不许。所谓不许治者不治也。
傅山的书、画、医堪称三绝。那不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也是心灵的慰藉。然而,晚年的傅山对此常常流露出厌倦和懊悔之情。他曾作《墨池》一诗,写道:“墨池生悔吝,药庋混慈悲。子敬今犹在,真人到底疑。佳书需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笔于今老,焚方亦既迟”。乾坤已病,人心何能医?俗物满眼,佳作与谁赏?真乃一生辛苦事,到底皆枉然。历尽沧桑的傅山终于抛开一切,平静的接纳了那纠缠他一生的宿命般的孤独:水落石出,一身廓然,所有尘世的荣辱喜乐,无数熟悉的、陌生的面容,还有那似乎没完没了的谒请、告求、恭维、艳羡……都随作了过眼云烟。
一六八四年二月初九日,傅山的独子、五十七岁的傅眉因病辞世。时年傅山七十有九岁。傅眉少秉异才,壮怀激烈,而终究抑落不得其志。几十载风催雨逼,他既要担承多事家族的重任,又要护持伟大父亲的风标,还要追寻自己难以对人言说的梦想,然而他呕心尽瘁,无怨无悔。他们父子是师徒,如兄弟,似朋友,像两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一起撑起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如今天倾一柱,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心境的悲苦可想而知。肝肠寸断的老人以血泪研墨,作《哭子诗》十六首,为后人留下了与颜真卿《祭侄文》相颉颃的书法绝品。人们会认为傅山其时一定长歌当哭,我却宁愿相信他在连缀词句、挥洒笔墨的时刻是宁静、漠然的:没有神明可以求告,没有知己可以诉说,只能以风烛残年的双肩承担起一切,默默地把无尽的伤痛雕琢在时间的大理石上。《哭子诗》长卷如悲风扬波,于浑脱中逸出凛然骨气,很难想象出自年近八旬且遭受致命一击、并仅于四个月后便长辞人世的老人之手。只有经过长期孤独煎熬、锤炼的非凡灵魂,才能在苦难面前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和美!
一六八四年五月,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傅山写下了跟这个世界的道别辞——《辞世帖》: “ 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
这是他的绝笔。六月十二日,在经历了近八十年的尘世风霜后,他淡定又决绝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赤裸裸归于自然,不带走一片文化的丝缕。大师远去,天地为空;片峰青伫,一龛霜红。
傅山曾模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为自己摹写了一副传神肖像——《如何先生传》,称自己是一个“如之而已”的“不可何之者”:为儒者却不讲学,为玄者却不能无情而长生;学禅家却不“捣鬼”,学名家却甘自为宾;知兵而不喜杀人,知墨而不能“爱无等差”;能诗而耻为词人,能文章而不慕浮华;孤光自敛,不涉臧否;有所大是,又有所大非;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不能忘情而“忘我实多”。总之孤蓬自振,片云独飞,廓然无所容,茫茫然无所措手足。
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相比,傅山的思想资源无疑博杂得多:他不仅超越了理学与经学的藩篱,而且博采诸子,出入释老。他反对经学的正统和独尊地位,主张经、子平等。从《霜红龛集》看,系统评注诸子是他学术研究的重心所在,对于一般儒生无意涉足也不敢涉足的《墨子》、《公孙龙子》等,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并多有独到发挥。对于经学内部的争议,诸如“今古文之争”、“汉宋学之争”、“程朱陆王”之争等等,傅山的态度是视若等闲,置之不论。只是在思想和情感倾向上,他还是侧重于“直指本源,勇于自任”阳明一派。他曾评价朱熹在“精神四射处”逊色于阳明。然而,对那些扎实、厚重的真道学家,傅山也表示了应有的敬意,如对河北大儒孙其逢,他就叹赏不已,称他“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不似腐儒“一味板拗”。总之,对于所能涉及的一切思想资料,傅山都是本着切于实用的原则,兼收并蓄,唯我所用。在思想视野的广度上,实在难有时人能与比肩。
傅山思想的理论基础还是以道、释两家为主。当他宣称自己的观点为“反常之论”时,判断“常”与“非常”的标准,还是传统的天道与人性的“自然”。他所谓的“常”毫无疑问就是不正常的,指的是因年深月久的熏染而被习以为常的、违背人性本然的东西,则傅山之“反常”,只是摆脱已腐败的文化(纲常礼教)对人之本性的遮蔽和扭曲,使之按照其本然状态呈现和展开自己。因此,尽管傅山对专制王权的批判异常激烈——因此被当今众多学者列为具有近代指向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批判还是缺少实质性内容的,基本上属于老庄式关于人格自由与物类平等的诉求。与同时代的其他进步学者一样,他通过将“天理”还原为“物理”剥夺了君权的神圣性,又在“万物一体”的基础上通过人之类属性的发挥伸张了平等的欲求。可以说,傅山反专制主义的思想基于“因自然”,始于反“奴性”,终于爱“众生”。
我们知道,西方之“近代性”的最突出标志,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体的觉醒。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从傅山这里看不到任何“近代的”的熹光——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流浪在异代的苍茫旷野里,在他和黎明之间,隔着的不仅是自然推移的时间,还有坚如磐石的文化壁障。也就是说,傅山仍然是传统体系内部相对于主流的“异端”,而不是得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者。
傅山注定是孤独的。在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看不到出路也厌烦了从前,只有随心所至任情发挥了:理无理之理,法非法之法;规矩由我立,风气自我开。他以渺渺之身面对茫茫天地,无适无莫,将“真”与“俗”打成一片,于艰难困顿中保育一脉天机,却被误认为名士作风。“但是跛陋石,唐颓总可人,风雨兼磊落,烟雨渗精神”,他把自己看做一块被遗落于天荒地老之中、百无一用却精神耿耿的顽石。有人把《红楼梦》的著作权归于傅山,看来不是全没道理:大荒山青梗峰下女娲遗落的那块补天石,独自经受了亿万斯年的风霜雨露,渴望着幻入红尘有一番作为,却耐不住其中的污秽和平庸——那不正是傅山的命运与人格精神的写照?
如果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文化传统之残山废垒的守护者(他们作为文化正统的代言人致力于清理家底、以待来者),傅山则在一度流连之后,越过了这残山废垒而走进了本体性的生存之中:天地茫茫,万物化育,人类耕食凿饮于其中,一体平等,小人与君子相待,犹无理与有理相生。在论及古今之变时,他说:“昨日新,前日陈;昨日陈,今日新;此时新,转眼陈;大善知识,无陈无新”。他对陈腐学术传统的声讨是以天道的“大善知识”为依据的,他对专制王权的批判是以“道观万物”的大悲悯为前提的。他之所以没有离世高蹈,只是因为“鸟兽不可与同群”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者,流浪在风清月冷的文化废墟上。他一生中非常随意地给自己起了那么多的字号、署号,正是身份认同之缺失的表现:茫茫天地间,无依无靠一过客,随遇而安,随意而名,无可无不可,有名而无名,留下的不是事业,而只是飞鸿踏雪的印痕和狂狷傲世的传说。
作者简介
李宪堂:(1966-),男,山东安丘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